夜读 | 衡水vs北大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学教育
F:今天咱们的讨论的话题叫做“衡水vs北大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学教育”。其中比较核心的还是“中学教育”,但是我们可以先来讨论一下我们当前的中学教育是什么样的、它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再聊一聊这背后体现出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或者需要,这样最后我们就可以来畅想一下之后的教育改革,思考一下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中学教育,包括比如说现在的新教改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啊,如此等等。那么我们的讨论,可以从这两个中学开始。这两个学校是比较典型的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代表。而且很巧的是,这两所学校都在几个月内有一些重大变动,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这会不会是一个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对立的时代的终结。即,以前我们一直以为这两者的对抗,应该是一个战胜另一个,但是问题是它们俩同时坏掉了。不管怎么样,现在其实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抛开二元对立的思维,去看看二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但是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说咱们这个讨论其实可以不用局限在这两所中学。我是北方人,可能对这两所学校比较熟。但是像什么深中、华师,我就不太熟,所以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学校情况,主要可以就它的特点、它的一些“理念”、它招了什么人、又培养出了什么人来谈谈。大家畅所欲言吧。
首先要有生源、师资和成绩作担保
T:衡水并不都是做题家。重庆南开中学是一所市重点,它会给一段专门的时间进行课外活动。但一切都是建立在高考成绩的基础上的。如果像某一所南京的中学,高考成绩下来了,那么改革就必须停止,这算是合法性吧。但是你说这种课外活动真的没有用吗?也是有的,因为看上去就是确实有很多人进入了北大清华的自招。
X:有个老师去了衡水进去考察,发现衡水的秘密不在于军事化管理,而在于师资力量和生源。师资可以帮助学生整理题目。而生源导致了其他学校相对实力下降了。但是有些老师就是因为生源质量下降而骂学生。我复读去的是一个大学校的复读班,就感受到了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们会重点讲很多压轴题。以前的老师发朋友圈,说压到了题目很开心;但是复读班里面的学生就天天能做这种题目。
Z:很多人也会说,衡水在河北省也是一所超级中学。衡水命题的水平确实很高。虽然管理方式可能有不同,我的学校宽松,衡水是军事化管理,但是可能关键还是在于师资水平问题。
T:衡水似乎是一个近几年的话题。再退10年,好像就没有那么有话题性了。它似乎是先用复读生和老师打出名气,然后再垄断生源。这种垄断之下,也许不能证明衡水的水平很高,或者二者是一个循环。以前我们的普通中学有一些好学生,但是现在录取分数线都不太行,老师都没有欲望来教了。而且,甚至老师也在被挖角。这样,反而让小镇学校变得更军事化。
Z:十几年前其实有纪录片讲这个事。《高考》里面就是毛坦厂vs深中。

《高考》剧照
F:现在政策收紧了,垄断生源没这么容易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衡水一中脱离衡水体系的新闻。
Z: 而且衡水中学还会开新疆班、少数民族班,用他们的高考加分来出成绩。我听说有些衡水学生来了广州高考。
Y:我记得当年那是有一个深圳学校把学生都送去衡水,然后去进行竞赛。最后纸包不住火,那年竞赛推优被取消了。
T:去年天津高考第一名也是衡水的。现在可能只是有所收敛。
F:天津是一个减负落实得很好的省份,所以那儿的学生考不过衡水学生也很正常。
Y:我们学校的高一高二也会有活动,然后高三分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区。然后生源上也有跨区招生,但是似乎不违规,只要签约就可以合理地进入我们学校。我们学校也受打压了。我觉得打压有好的效果。我们学校是私立学校,本来是出状元的,但是两三年之后公办学校也能有状元。我觉得只要打压到一个度,我觉得就很好。
F:能不能具体说说?
Y:我们的上课时间被限制,周末和晚上不能上课。暑假和寒假精英班本来是寒暑假单独上课的,但是现在不允许了。
T:我们学校跟大部分学校一样,各种补课。有些县中学就会更卷。很多人都自发地想要去更好的学校,我就是。当政策下台之后,有一些很绝的方法。比如说从小学挖起,初一初二初三各挖一轮。然后就是建分校,单独招生,然后把优质学生再放到本校,成绩差的花大钱在分校学。这就像一张网一样。我们初中还行,但是优质生源,其实都抢走了。
其次才是不同教育模式的比较
Z:那么,我觉得重点更是,教育模式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都知道生源重要,但是如果想要比较两种教育模式的话,我们应该控制生源这个变量。
J: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学校都是精英,那问题就在于我们要怎么样培养一批精英呢?我支持王铮,因为高考的解题能力在高考前几个月就差不多了,所以高考复习应该用一年就比较够了。
T:但是这前两年真的有用吗?前两年似乎只能让精英中的精英变得强大。而且高二升高三会是一个坎,大家会有压力、心态转变会很困难。
J:我觉得如果这个转变会造成压力的话,那么这可能是值得的。这就像,你晚上蹦迪,虽然早上痛苦,但是你觉得这是值得的。
Z2:那么,有没有可能高一高二学生也会自己转变呢?有没有可能他们的高一高二没有那么自由?
C:对,北大附有的人就说他们白天才感觉在上大学,晚上还是上高中。

Z:对,而且北大附前两年真的更好吗?这个也是及其有争议的。
Z2:我觉得应该反过来比较好,第一年猛学,第二年第三年自由学习。
T:但是做题技巧会流逝的,所以还是要在最后一年吃苦,要不然高考考不好的。
Y:其实不管是衡水还是北大附,我觉得讨论教育模式的标准,在于我们希望教出什么样的人。衡水没有考虑到高考之后的人生,但是北大附看见了,所以他强调了素质教育。如果这么说,我们会自然地认为北大附更好,但是有一个现实问题:很多时候,虽然那几分没那么重要,但也是会决定资源分配的。高考的分,决定了你去哪个大学,影响了你以后的人生。这就很冲突了。我为了未来的素质不要的这几分,值得吗?
J:我觉得“三年高考”其实并不是必要的,可能会有边际效应。而且,另一方面,虽然素质教育是难题,但是这不是可以逃避的,中学逃了还是要在大学补回来的。
Y:我其实没有彻底对立的意思,我觉得二者都有点极端。衡中太卷了,北大附太松了。北大附应该照顾一下现实。
T:但是确实有成绩下降。但是,我觉得这种大量花时间办社团还是很奢侈的,这是高分学校的特权。
F:应试素质也是素质。而且北大附现在的样子其实也是照顾了现实、进行了妥协的结果。毕竟北大附的教育理念是公民教育,如果不花一两年的时间学习民主管理,这种实行自我管理的能力怎么培养出来呢?
Z:不仅是北大附他们的课程,其实可能北大附的自我管理可能更会带来素质的影响。包括改组学生会这样。我觉一般应试就不会允许这种东西的存在,因为自我民主管理的能力不回带来成绩的正面影响。
L:我觉得区分不在于什么样的教育,而是教育还是不教育。应试应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但是现在应试被异化成了目的本身。而北大附就呈现了一种割裂,它高三的时候告诉我们,你要晚一点再教育,你要先去好学校。这就有一个叙事上的割裂:我们的意义究竟是高考,还是未来的人生?我们一般学校叙事,都是让学生先通过筛选、之后再寻找人生的目的。但是,这个东西可以拖延,但不能逃避。
C:那我觉得你预设了教育的应然形式。但是教育是现实的。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的每一刻都在实现自身。所以简单的应然是不靠谱的。北大附之所以是北大附,它的再生产是什么样的?它的持续存在是何以可能的?这可能就跟社会权力有关。衡水需要成绩来维护权威,而北大附或者深中有一个单独的原则,比如素质教育这个原则,它能在社会中单独来维护权威。
Z:北大附的原则基础其实不坚固,因为有很多家长还是看中分数。别说家长了,高三老师都不喜欢王铮。我觉得这个可能和王铮这个人有关,他的个人权威可能会对这套模式的存在有很大影响。
C:对,我们之所以能谈这个,是因为它们都是中学,最终都是升学率说话。
T:但是这是在不断妥协的。有些人想要用自己的努力影响一波学生。这就有点像某高校的博雅学院?学院在两位领袖离开之后,就一蹶不振。这是不是个人的教育理念与社会的对抗?但是往往不会有很好的下场。这种努力我是认可的,但是最终未必可以成功。
L:现在我们的土壤就是社会不平等,所以唯分数论还是现实的。
C:我不理解这个冲突。如果讨论博雅学院的话,他们的失败可能还是主要在于自己没把课设置好。
T:那这种“自己没有做好”,是不是也是因为一种“器官移植排异反应”呢?
C:但是,就比如历史系,就需要接受古典学教育,它和博雅还算比较接近。
还要破除公民教育和城乡对立的幻想
F:也许我们可以多谈谈北大附中,毕竟主题是中学教育。
C:北大附是学分制,他们的课程是学分制,两年的学分和咱们四年一样。而且有的课就突然就没了。这是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把知识传播给学生的方式呢?
T:但家长之所以会信北大附,是因为他们希望有一些新东西。我们现在就是备考——进大学,但是王铮冲击了这个价值观念,而且他是逻辑自洽的,所以我们才会支持他、希望他成功。
C:我觉得这个……18年那个北大附的视频,它能拓宽人们的想象力,而不是一遍又一遍地让权力加强它自身。可能很多高中都采取应试教育,但是他们连应试该怎么做都不知道。这就是一个关于要怎么做的规定。
X:你说“考试为了升学”,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1949有高考,66年暂时废除了高考,给的理由是只有比较有钱的人才有可能进行高考。我爷爷是农民,他就是上不起学——而知识分子的孩子就可以自我教育,然后成为新的领头羊。所以当时的领导人认为,这样工人的儿子还是工人,农民的儿子还是农民。所以当时推行了上山下乡的政策,它希望所有人都可以享用知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78恢复高考,受益者还是以前的知识分子。那些知识分子的子弟就能再次进入学校,然后拥有特权。大家都是努力,都是建设国家,但是却因为家庭背景却造成了差距。我们重视高考,是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能进入更高的阶层。我是农村的,我以前就是玩游戏,不好好学习,但是有一天突然就认识到成绩的重要性,所以就拼命赶超,觉得成绩差就是低别人一等。后来我复读进了这里,就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了。现在王铮说要搞公民教育,可能是在对抗分数体系。但是这可能是不足够的,因为分数联系文凭,文凭联系待遇,这背后是不公,是贫富差距——这不是搞公民教育可以解决的。
C:你说的高考如何决定人生,可能是从社会地位来考虑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了公民教育、艺术教育,这确实是对未来的生活有用的。
M:但是,北大附在北京,衡水在河北。这有一个教育资源的差距。我们需要联系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来讨论。
C:我不是说这两者产生的后果是一样的。
X:那些有钱人的孩子学习公民技能,是因为他们后来真的用得上。
F: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北大附学费不贵,录取方式也很公平,里面的学生也并没有比北京其他学校出身于更高的阶层。
W:它实际上没有,不代表它的理念不是。
Lv:但是你这么说,你反而没有破除这种城乡对立的幻想。衡水的学费可是比北大附贵的,北大附的学费就是普通公立高中的学费,衡水学费可能会达到10w。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北京人、天津人去衡水读书。我们也应该看到,北大附模式也是有基础的——你高考就算没考好,也是会有出路的,大不了出国,或者再回去复读(虽然实际上不允许)所以肯定有一个基础。但是这种基础,能证明北大附在培养继承人吗?北大附或者深中如果说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悲剧性,其实是在于没有真的培养出继承人。它们比较像19世纪俄罗斯贵族的学校,日本明治时期的帝国高中。但是在今天,如果我们这么指责北大附,一对比我们就发现,它和那些真的贵族学校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是说回来,北大附培养的学生,相比于流水线生产的学生,还是有价值的。但是由于我之前提到的原因,它还是具有悲剧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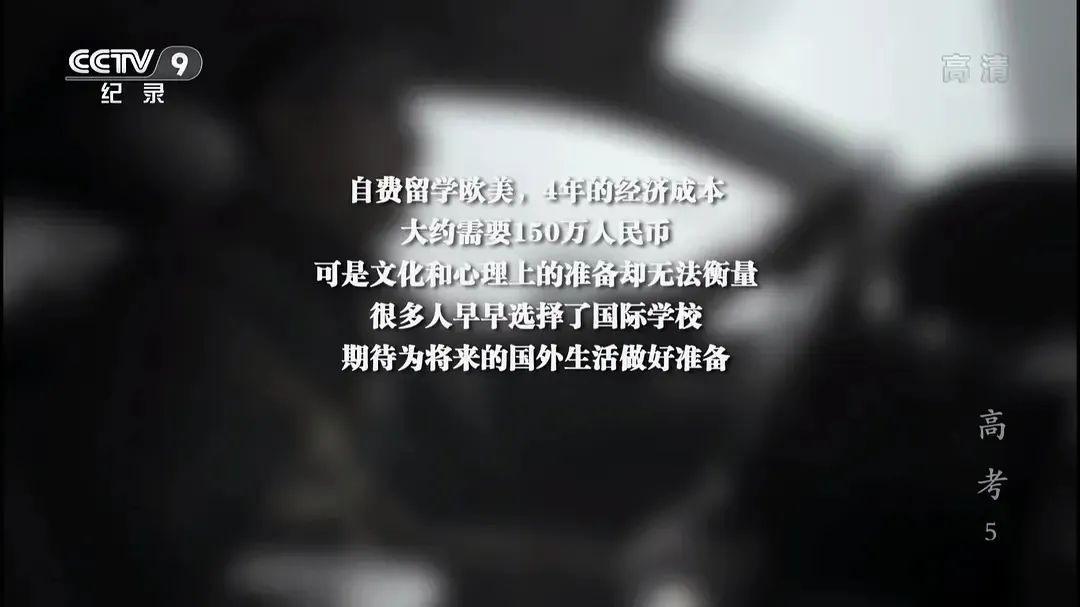
T:这二者都是当地比较好的地方。衡水里头也都至少是中产。那么,我觉得可以从地域特殊性出发,河北分数紧迫,所以卷;北京分数不紧迫,所以松。但是可能在其他地方并非如此。很多乡镇中学,就既没有素质教育,也没有应试教育。
C:我有点懵,咱们讨论的是学校的对立还是模式的对立?后者的话,那北大附肯定是奇葩啊。
T:可能在北京,有不同的观念。
F:其实很多学生进了北大附不是因为家长接受北大附的教育理念,而是因为家长不了解北大附的教育理念。
X:这种悲剧性可能还在于,这种公民教育其实也不会让大环境更好。
Y2:承接刚才C说的,我的看法是,虽然这有一个谱系,这两所学校在光谱两端。我觉得衡水是靠国家,因为他们最能参透国家的考试体系。我们就算不讨论职高、二本、三本。我们还有民族问题、国籍问题、私有公有问题,这里面其实都包含了国家制度设计的问题。在改开前,那这是为之前那种生产服务的——教育都是为当时的社会、当时的生产服务的——之前国家的的想法在于,分散教育资源,放弃教育重点化。日本、俄国、今天的中国都是重点化的。那么回到衡水问题,这沿袭了国家性的问题——中国的高中不一定就要接中国大学,也可以接外国大学。老师也是如此,很多老师的想法都是多元化的。但是国家最终没有选择多元化发展的路子,所以一元存在就压过了北大附的多元。某个高校搞博雅教育,也是个怪胎。北大附也是怪胎。这些怪胎就有特殊的成长路径。这体现了社会转型——国家的强势到资本的强势、房地产的影响、地方政策……西藏的民族政策不也是如此吗?虽然国家政策一样,但是可以从西藏地方制度动歪脑筋。但是呢,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国家要重新接手教育。我认为国家应该从整体上考虑,先理清教育的思路,不过,我觉得能不能达到这种效果还得看这两年的具体操作。

Z2:我有一个例子:双改之后,学生还是很晚睡觉。
Z:对,只是改了时间,没有改变评价体系。
C:我正好就在做家教。我教的那个小朋友就要在五年级学剑桥英语和编程。然后6年级就面试。谁家更卷,谁就能抢到资源。
J:但是其实现在小学教育都有点像北大附吧。我听说现在云南有那种实验式学校,不学应试,学农业、艺术。
Z:但是不唯分数论就是北大附吗?
F:这是不是恰好相反?听上去,北大附是帮你进入社会,而云南的小学是保护你不进入社会。
L:这有没有可能用地方知识来解释?
J:我强调的是非唯分数论。虽然可能有点不现实,但是我们在给孩子讲故事,教给他们如何做人,我觉得意义是积极的。
T2:有人知道具体教啥吗?(大家回应有人文、艺术、科学等课程)
C:但是唯分数论与否,不是能选择。
Z2:那有什么能选择吗?
T2: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幻想,我考了什么分数,就能上好大学、取得成功。所以这是少数人的游戏。
Z:难道这不是衡水的学生的幻想吗?多元教育的基础就是有不止一条路的选择。
F:有没有可能存在信念和现实的偏差呢?
那我们为什么非得在一条路上挤破头呢?
Z2:而且现在物质条件充沛,凭什么我们还要拼命去竞争呢?
(大家:生产关系问题/有人拿走了你的东西)
Z2:如果我们不拼命竞争,我们的处境真的有那么不可忍受吗?
T:总体经济的增长和个人收入的增长是有不同的,不是国家经济上来就不需要竞争了。
L:我发现,我认识的那些认为不读书也可以过上好日子的,都是那些潮汕、温州的商人家庭。我在读一个温州人聚落,他们的孩子就不读书,因为他们的家长就通过另一条路(做服装)获得了更多机会。
C:我教的那个小孩家里也是做服装的,但是他们家里存不住钱,所以他才要如此努力。而且其实还有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选择。
T:他们只是被迫当了体力劳动者。而且,我还发现,虽然现在高学历的作用在逐渐降低,但是人们还是认学历的。
Z:职高的建设很不完善,有那种黑工厂就用职高当学生工。
Lv:这是有历史基础的。我家长是国有工厂的工人。那十年虽然让工农容易上大学。但是那个年代人们更愿意读专科,子承父业,进入纺织厂。我妈想读专科进厂,但是我姥姥想让她读师范。刚刚改开的时候,情况又有变化:很多那时候上大学的教授都说过(比如戴锦华教授),在当时,都是学校求着你保研。好多学者都下海经商了。
C:我觉得我们对于升学的视角就非常单向度,没有考虑职业教育这方面。
Z:这是话题决定的嘛,中学教育而非专科教育。
J:我说个无端联想,我最近在看一本书,他说“我不明白一个教师的工资为什么比纺织工人高,因为教书比纺织有意思多了。”
L:欸,还真有人研究教师的幸福感,说教师和照顾病危老人的工作的幸福度是类似的。(笑)
J:我的同学都把学习和生活当成两个世界。
C:对,但是进厂务工,你的生活和工作就是一个世界。
但是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中学教育?
F:对,这就谈到了一个老师的维度。一所中学包括了学校、学生和老师,如果要谈中学教育,应该三者都要谈,我们之前的讨论可能没有很重视老师这个维度。
W:王铮就是学生和校长治校,所以老师就是非常不满意的。如果把学校看做教师参与的共同体的话,那确实……但我们其实还是更重视学生的被教育和被管理。
C:对,老师的教育工作可以不是目的,但是学生的受教育必须是自己的目的。教师每天都在接触被教育的具体的人,但他们必须用统一的标注去规范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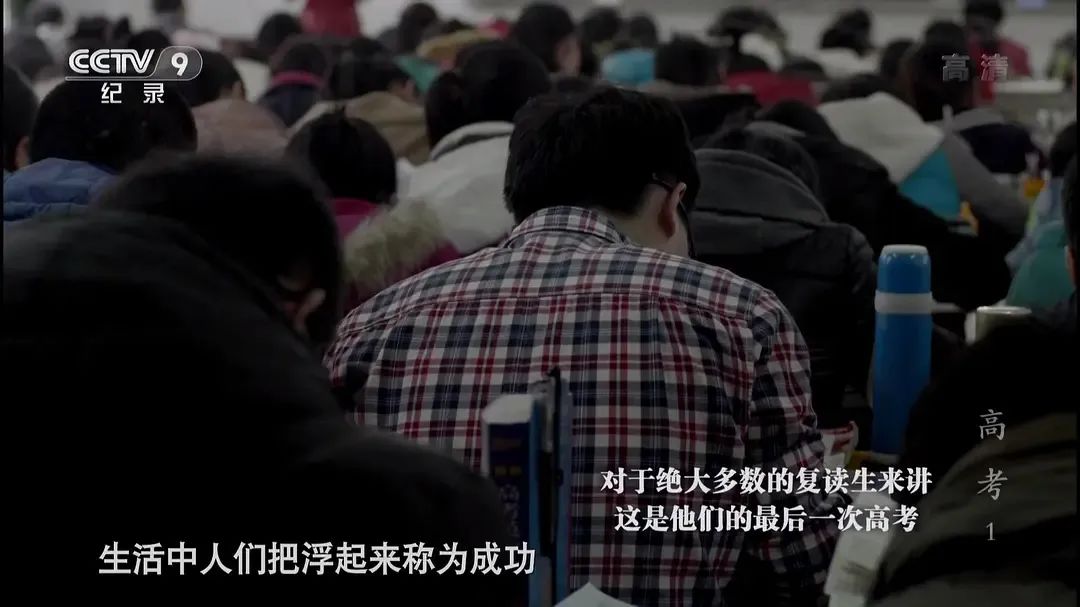
X:我想起以前的志愿者团体:他们是大学生,帮中学生了解专业。他们很保守,就是像着单纯传递一些知识,补足中学的缺失。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必须正能量,不能说专业不好。所以就是的宣传了。我之前跟他们说一些性教育的问题,但是不符合正能量,于是就被拒绝了。之后我就和他们分开了,我们成了流亡者。我觉得,不应该在两个模式之间二选一。比如说,我们可以教育一些大学专业内容。
T:对,但是很形式化。这是新高考的要求,但是大家只是执行命令。
F:对,就比如我们高中的职业生涯规划课,那个课是我上过最烂的课。
J2:而且我们还需要考虑,这种在中学阶段帮助学生了解大学内容的做法,真的有效果吗?我高中就很喜欢社会学,但是进来之后我才发现大家都在搞定量。所以光靠这种宣传有时候会有点先入为主或刻板印象,很多时候自己试过才知道。
Z:对,但是北大附的教育会有实践的。我们学校就有论文的作业。但是如果所谓的职业生涯规划只是任务性的讲述,那就都是场面话了。而且,我觉得我在高中的一些进步主要还是来自自己。
TQ:X,你为什么不去其它组织宣传真相呢?
X:得了吧。另一个组织教出来的学生,我问他大类招生如何,他们说“挺不错的”。
T: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点,就是我们虽然没有规定,而且我们自己不喜欢大类招生,但是还是好话说的多。
L:在高中时期的学生心里,大学就是个光环,说某大学就是樱花,恋爱,哇!好!
X:有没有可能是无意识维护学校?
大家:有可能。
X:就比如性侵犯,大家都夸学校处理得好。
T:而且,我们对大学生活还是有不错的评价的。
Z:至少比高中好。
F:说到这个,我就想起北大附分校装修材料不合格的事情。当时大多数学生都在护校,在攻击报道这个事情的公众号,只有少部分学生在关心那些因为不合格的装修材料而手上的学生、要求学校解决问题。这么看来,北大附的公民教育也没教出多么有自觉的公民。
T:但是护校会不会是公民教育的结果?因为一般学校没那么护校。
X:非也,我觉得普通的学校都会有很强的学校认同,很多人都为自己高中自豪。比如说,有人在六月的某个日子就把自己的微信头像换成自己高中的图片。
Y2:我听说香港小学生在路上发政治性传单。北大附中护校可以看出一些政治意识,自为的政治意识。以前有一段时间,中学是政治化的;但是现在的国家就不需要中学很强的政治意识。所以这就是个问题:需不需要政治意识。香港的那些小学生,他们真的应该拥有政治意识吗?
Z:我觉得公民意识、或者说自为的政治意识,反而会让学生不无脑护校。因为这是一种自发的身份认同,别人骂学校,你就觉得自己被骂,所以不允许自己的学校被骂。香港好像确实有这种东西,我不喜欢。但我觉得公民教育也不是像香港那种,这种反而没有啥政治意味。
F:好吧,时间也差不多了。比较可惜的是,我们最终也没有讨论出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公民教育,不过,我们就以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结束今天的讨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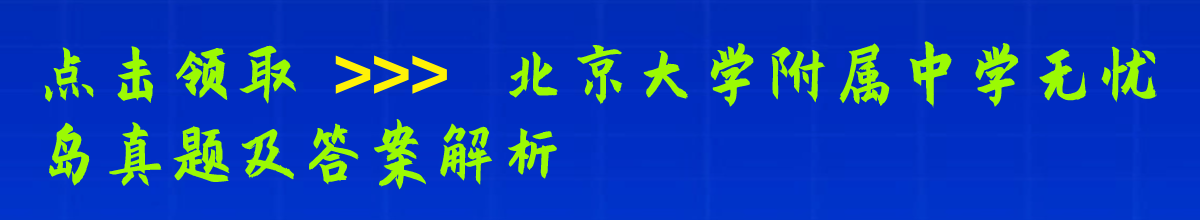



全部 0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