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杯优秀作文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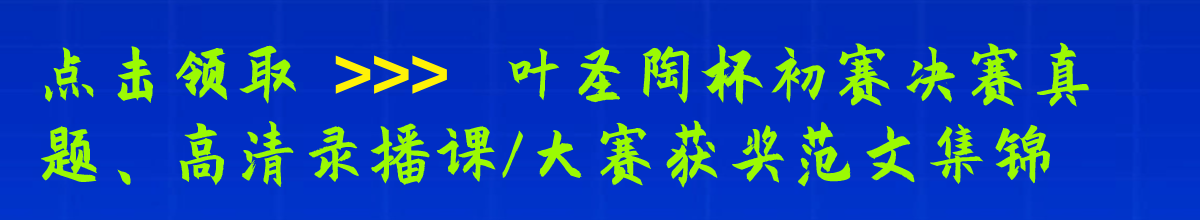
叶圣陶杯优秀作文展
第一篇:泉头泉记
高一22班 刘治平 指导教师:王慧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题记
泉头泉,位于薛城城区西北10公里的泉头村,60年前刚刚使用自来水时这就是自来水的水源地,而今也是薛城的一个人文景观,有着美丽的传说,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一大增色之处。泉所在的村落就在外公家的前面。
趁着周末,我和外公前往泉头村,去实地探访泉头泉。
远远地望见一个石亭前,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两旁各有一头石象,石亭四周绿水环绕,亭前一块石碑赫然写着“清代第一新泉 泉头泉”,走近了看,亭子中央是一口凸出来的小井,里面有水潺潺流动的声音,置身亭中,能够感受到泉水缓缓上涌的清凉。外祖父指了指亭子侧面玻璃罩上的两块石碑:“那就是皇帝留下的”,加上底座,石碑约一人高,隔着厚厚的玻璃可以看到,花岗岩的碑身斑驳不堪,一座碑已经裂成两半,似乎在向世人诉说历史的风沙卷息,因年代久远几乎无法辨认字迹,上面依稀刻着“黄沟 第一新泉 山东通运清平道 乾隆六年九月”一算,距今有了整整280年的历史,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种历史的厚重感。石亭边还有一眼小泉缓缓流淌着,沿着一条石径进入水渠。这就是泉头泉的源头,流向村头,流向微山湖,流向整条京杭大运河。“泉眼无声惜细流”,清朝存在275年,人类出现不过300万年,但这带水系已经流淌多久?几千万年,几亿年?答案只有她自己知道。我坐在泉边,仿佛时间不再流动,这大千天地都凝在这方寸之间。
凝思中无意回头望去,只见亭后的墙上印着习总书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儿的环境保护的很好,没有污染,附近的河流都清澈见底,四周的杨树高耸挺拔,阳光透过树荫的缝隙在地上洒下斑驳,我看见秋风从树梢穿过,引起了一片鸟鸣,于是想起陶公所写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在如此快节奏的社会里,保留了如此的一方净土,实在让人有心旷神怡之感。
“听祖上的人说,清朝乾隆年间,从黄沟到微山湖,大半个山东都是被淹没的。乾隆皇帝下江南,在这儿盖了个金盆,想要把水都收了,皇帝金口玉言,于是这边水都被镇住了,但地下流的水多旺啊,禁不住地往上涌,于是就有了泉水。乾隆皇帝立了个碑,从此就叫泉头泉了,顾名思义,泉头就是泉水的发源地。”
外公顿一顿,喝了口水,又接着用嘶哑的声音说:
“这段水呀,从黄沟一直到微山的八里屯,一共七十二个井,每一个井立一个碑,京杭大运河缺水的时候都得靠它来填补,这一带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这里的水长大的。这一带有九个井眼,但时间一长,就只剩这一个泉头泉没有干涸… …”
回去的路上,外公让我注意一栋建筑。“那是自来水厂,整个薛城,甚至整个枣庄市的水都来源于此,这儿有纯净的地下水,所以是水源保护地。五几年的时候,在这里开发水厂,第一个钻杆刚下去,水就猛一下子涌出地面两米多高。”
这一口小小的井眼,从隋朝开始补充着大运河的水量,一直到今天,仍然为我们提供着洁净的自来水,望着满面皱纹,白发繁鬂的祖父,我终于明白了。
生命的价值不应用时间的长度衡量,而是对这个世界的价值,正如法国数学家帕斯卡尔所言:“给时光以生命,而非给生命以时光。”如同一眼泉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才是生命最本真的模样,不言不语,默默付出,我从外祖父的眼中也读到了这一点。泉头泉如同这片土地上的守护神一般,滋养了一方人,荡涤了心灵。正是有了这清澈的泉头,才有了那万千活水。
是为记。
第二篇:在铁轨上
高三21班 袁子暄 指导教师:刘宏
我是在铁路旁长大的,火车的轰鸣是我入梦的童谣。
清晨它与太阳一同到来,悠长的鸣笛划破黑暗,唤醒尚还寂静的小城。于是火点起来了,烟烧起来了,早餐摆起来了,我从酣睡中苏醒,迎着朝阳奔向学校。午夜时分它悄然入梦,像怕打搅人们的安眠,鸣笛声也熄去。我有时夜半惊醒,听见它驶过的声音,便重又安心睡去,仿佛枕着铁轨入眠。
而我最常与它相遇的时候,是日暮黄昏时。我蹬着自行车回家,它总准时出现。我数着火车的节数,在楼旁的小沙堆上用草根记下一个数字:23,第二天仍旧数,然而却忘了记录,待想起时,上次的数字已被风磨平了。我回头,便看见太阳迷失在云堆里,与此同时不知何处飘起了悠悠的歌声——“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我不懂歌的含意,只是在余晖与歌声相伴中归家。
待我再大一点,便时常爬上那高架桥上的铁轨,颇有些登高怀远的意气。脚下是如川的人流,在日暮中欢涌着。轨道两侧生着人高的茅草,秋天会抽出雪绒般的“花”,如白云揉碎一地,又轻似飘乎的梦。顺着铁轨极目,远远能看见群山,已在日光和烟气里浮成孤寂的暗影。很快去夕阳西下,灯一盏盏点起来了,又听见火车那一声长鸣,号角一般。赶快从铁轨上下来,躲到一旁的碎石子上,火车便哗地闯入了——一节,两节,三节……是空载,倦鸟归巢。
火车是从何处来,又将之于何处去?这是缠绕了我一整个童年的疑问。在高架桥上远眺,光滑的铁轨弯成一道优美的弧线,伸向天边——天边,这就是我的答案。要爬上火车与它一同远去的愿望日益灼烧我的心。
又是一次火车经过的时候,父亲告诉我,这火车是确乎能爬上去的。此时,耳边又一次响起了那首熟悉的旋律——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一段悲烈而雄壮的历史图景在我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
八十多年前,在枪林弹雨淹没整个村庄,炮灰和硝烟几乎把太阳吞噬之时,一群衣衫褴褛的工人站了出来,组成了去鲁南军区铁道大队。就在这条铁路上,他们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1800多个日夜,在土琵琶的乐声中,在层层芦苇荡下,他们扒飞车、搞机枪、撞火车、炸桥梁,截获枪支药品、毁坏运输通道、阻断情报网、护送干部往返延安,围困敌军三日耗得对方弹尽粮绝,最终装备精良的千人日军受降于不足百人的游击队。从此,微山湖水波终平,峄县重归安宁。
于我而言,那是一段不输陈涉吴广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乃至巴黎公社的伟大历史。从此,火车在我眼里肃穆起来,走在铁轨上,心中也不免多一分敬意。
后来我搬离了那条铁轨,离开我的旧友,而住得更接近高铁轨道了。我看着那些优美的流线体动车,影子一般飞向天边,飞向未来。
多年以后,我再次站在那铁轨上,望着夕阳。听闻它即将停运后,我总觉得它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衰老。听父亲言,微山湖曾是一块陆地,为汉相张良的封地“留城”,直至某日城门口石狮双眼猩红,留城轰然沉入水中,遂为微山湖;又闻言,此城六十年一现,一老农赶集时大雾弥漫,误入此地,环视四周只见货物不见人影,遂携一铁锅偷偷离去,待回家时才始知铁已成泥。如今,这铁轨竟与那微山湖一般,有了几分沧海桑田的意味。它依旧沉静,俯视桥下熙熙攘攘的人流。它见过多少人的呐喊与痛哭、狂笑与啜泣啊?而它不投以任何悲悯,只抱以沉默的注视。
啊,笛声,火车来了!它如一位年迈老者,缓慢而铿锵,从我眼前驶过,它将驶向何方?长大后的我已知晓它所连接的地区与我生活之处并未有什么不同,但当我极目远眺,我的答案仍是———天边。
茅草被染上了金黄,安静地陪伴着那些已逝的亡魂。绿意却逐渐茂密,遮住了那苍苍白发。我看见那火车不断加速,化为银亮的飞鸟飞向远方。且让那过去成为滋养和供给吧!纵使三度迎来落日,我们仍将伴着英雄血,走向天际。
第三篇:落叶归根
高三19班 王放 指导教师:王丽娜
当录取通知书送到王家时,王孝礼刚犁完地,将白汗衫脱了,坐在埂头的大磨石上抽旱烟。
他身旁矗着一棵千龄有余的老槐,据西水王家族谱记载,此槐是宋朝先祖王曾连中三元后在此手植,并赋诗曰:“槐黄之月,身负书剑。持笔如椽,报国为先。天愍相材,连中三元。当成槐鼎,为生民见。”然而自王文正公以后,西水王氏便再未出过高于举人之名,但每代父辈都指着这棵槐树对自己的长子谆谆教诲,希望王家再出大才。
听到这消息,他立马蹦了起来,震惊和极度的兴奋让他的腰杆猛然挺直,双眼如老公鸡一般瞪大,嘴像村外二十里的大井张开,将烟杆子一扔,跌跌撞撞向家里跑去,一边跑一边朝天大喊着:“苍天有眼哪!王家终于出了个大学生!老祖显灵,王家的根还在这里!哈哈哈哈哈......”烈日让他的背上漉出一片汗,渗进皮肤的皴裂里,像久旱逢雨的土地。
跨进家门,只见妻满脸笑意地剥着花生,锅中飘来炖牛肉的香气;王孝礼的母亲王林氏在堂前踱着碎步,念叨着:“老头子......咱孙子争气,王家出读书人了......”,喜悦将她额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如过年时熏制的腊肉。看见王孝礼,妻向屋里指了指手,儿子王与义正在屋里看书,王孝礼大步流星地走到桌头,很用力地拍了拍儿子的肩:“娃真有出息!”王与义也很高兴,但克制住自己的激动,只是咧开嘴不住地笑。
那一晚,王家摆出全村最丰厚的席。待来祝贺的人酒足饭饱离席后,王孝礼揽着王与义,带着七分醉意三分清醒,滔滔不绝地和儿子说话,时而哭泣时而大笑时而高声呐喊,王与义以前从未见过父亲这般失态,一改往日沉默寡言的形象,直到凌晨三点才疲惫睡去。
两个月后,王与义登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临走之前,王孝礼对他说:“娃呀,走了就别再回来,学老祖在北京当官,家里面有你爹撑着,把心放踏实喽!”,王与义掩盖住心中的不舍和苦涩,挥了挥手便转身离开。
露从今夜白,万里故园心。
春夏秋冬又一春。转眼间五年已过去,村口的千年古槐在一次暴雨中被雷劈中,一夜之间已是枯萎不堪,连常在其上搭窝的灰鹊也飞离了千年的巢窠。而王孝礼的腰身也开始如庄稼人的命运一样呈现略显畸形的佝偻,风霜侵染上他本就稀疏的双鬓,加上前年发大水,赔上一整年的收成,使他看起来不像普通的五十多岁的老汉,更像一杆被凛冬压弯身子的麦。
这几年,王与义一直在给家里寄信,他在大学里勤学苦思,一直都是系里前三,甚至在校庆上被总理亲自接见。他给王孝礼写信说,自己受到黄文秀同志的影响,也想回来为家乡做贡献,但王孝礼坚决不同意,他在电话里对王与义说:“娃,爹让你读书就是想你别一辈子都面朝黄土,种地苦哩,求天求地求官,腰都累断了还是收成不好。你三大爷那回儿就因为遇上十年大旱灾,借的钱还不上,吊死在家里。爹起早贪黑这几年就是为了你上个大学,别待在这一亩三分地,死到头还是被黄土埋了,......”
这天,王孝礼正在田里施肥,青色的麦苗如海一般围绕着他,阵风吹过,他抹去颈上的汗,抬起头,忽地看到村口有一个人背着大包小包朝他走来,茁壮的身板和他形成鲜明对比,在十里之外就能看见闪闪发光的双眼,脸上带着盈盈笑意:“爹!我来搭把手!”
他终究还是回来了。
本来王孝礼看见儿子,刚想发火骂他,可是余光瞥见他衣角缝补得像刚被割完的玉米地,针脚又是如此粗大,不觉口气软了下来,叹息一声:“唉,你——你就是不听爹的话......王家的根看来是迁不走了......”王与义倒是笑呵呵的:“爹,娃这次带来了能让乡亲们富起来的方法,你等着瞧好嘞。”不在意王孝礼狐疑的目光,王与义接过父亲的肥,弯下腰开始忙活起来。
只有林间的灰鹊看见,已枯死的槐树上,发出了一抹新绿色。
辛苦考上了大学,竟然又回来种地!听闻此事,村里的人纷纷开始议论起来,有人不理解,有人幸灾乐祸,有人叹息,但王与义全都置之不闻。他先是跑一趟县里的水利局,请他们勘测了村周围的地形地势,确定了建输水管道的位置和引水地,接着又联系上通信公司要给村里通网。万事俱备后,只差一件事:交钱。
县里的财政本来就紧张,不可能拨出多少钱,王与义只得挨家挨户地上门募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没一个人愿意站出来。毕竟苦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攒些钱,谁愿意让一个毛头小伙子拿去做所谓“农村建设”呢?
坐了大半个月的冷板凳,王孝礼终于看不下去了,他召集全村人在村口召开会议。
“乡亲父老们,娃为什么考上大学不出去做官,还跑回咱这破地界?就是娃说想让大家伙都富起来,生活好起来!娃现在东跑西跑,找这找那,嘛子都办好了,就差大家交钱。我知道大家穷,拼死拼活在几个灾年也就攒下这么多钱,但不搞这些建设,咱会一直穷下去,老汉我这点觉悟是有的。”
“谁知道你家男娃能不能把这事搞好?万一搞不好了,大家的钱不都打水漂了吗?”
“就是,俺家这钱还是留给二狗娶媳妇用的,攒了三四年了!”
“俺家也是,这钱要弄葡萄架子,凭嘛搞这个啥都捞不着的什么建设?”
“乡亲们,请您们就信我一次,不信我,也该信党的领导和我作为一个党员的承诺!”
“好了好了,各位啊,如果娃让这钱打水漂,你们尽管找王家要钱,还不出来钱,你们把我王家祖坟刨了都行!这下还有什么担心!莫不成还要老汉给你们打条子?”
乡亲们开始窃窃私语起来,王孝礼平时在村里是有求必应,从不反悔,况且王与义还背着个“村委书记”的名号,可信度应该不低。
“中!既然孝礼老汉都这么说了,咱大家也都信一回吧,毕竟搞好了还是咱大家受福!”
听闻此言,大家纷纷点头,把自己积蓄的家底全部拿了出来。
就算如此,离尾款还差3万元,王与义一咬牙,向农信社贷了3万。
终于,输水管道接通了,全村也实现了网络覆盖。基于此,王与义带领乡亲们发展起网络农村经济,建起供销一体的加工厂,网络销售渠道减少了以往“丰年积谷穷”的情况,很快,村里就有人盖起了两层小洋房,汽车也开始出入村口,越来越多的人家能支持孩子读书上学。
王孝礼笑了,他终于知道,儿子做得没错。被这片土地哺育大的孩子最终回归了土地,贫穷终于离开了每个人的头顶。而村口那棵槐树,甚至重新生出新根,而且越扎越深,恢复了枝繁叶茂的状态,灰鹊也重新在此筑巢,鸟语啾啾,人乐融融,好一派和谐景象!
2021年7月16日,临近涧源村的黄河支流决堤,灾情十分严重,耕地全部被淹,由于洼地地形,洪水水位有上涨的态势,县里发布紧急通知,要求村民赶快避灾。
待全部人口转移至县郊附近的安全地带时,县委书记杨青清点人数发现,村委书记王与义并未在场。下午3点,王孝礼带着一队青壮劳力赶到,安排起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县委书记杨青问道:“王书记在哪里?”王孝礼沉着脸道:“与义和其他几个人去救援村南面的李家了,他们家只有一个寡妇和一个小孩,让我们先来安排救灾工作。”
站在地势稍高处,便能看到洪水的魔爪在疯狂撕扯着原本宁静祥和的涧源村,房屋的碎片、时隐时现的家禽的尸体、一袋袋本应销往外地的特色农产品,都在浪涛的席卷中淹没无迹。天阴沉翳暗,如人世间的黑全部凝在村子的上空,开始下起雨,开始起风。王孝礼呆呆的看着村口,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那棵曾庇佑过千年农人的神树、那棵曾代表着王家最深厚最希冀的根,倒了。
下午5点,县郊南出现几个米粒大小的身影,凑近一看,是厂长吴平和几个青年搀着女人抱着小孩,王孝礼几乎是疯了似的跑上去,劈头就问:“与义呢?与义怎么没来?!”
没人说话。
雨越下越大,这时人们发现者不是雨,而是罕见的雹子。
“说话啊!!你们倒是说啊!与义——与义呢?!”王孝礼无助而几乎哀求地看着他们,庄稼人一生最后的力气,被他点燃起来,只是为了看见自己的儿子。
吴平一边流着泪一边用沙哑的声音嘶嚎道:“老汉,书记......书记他......书记他在救援时被洪水卷走了......”
电闪雷鸣。只有洪水不断冲击着这片土地的刺耳声。
塌了。彻底地。
王孝礼“扑通”一声瘫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我的娃呀......”
2021年8月,涧源村灾后重建工作基本完成。省里面听说王与义的英雄事迹,特地派人前来慰问,并送来“扎根人民,不负使命”的锦旗。王孝礼形容枯槁,他只是把锦旗叠好,放在王与义床头。
墙上是一整面“三好学生”奖状,虽然破旧,但每张下面都盖着鲜红的共青团印。
还有一篇日记。
字迹已模糊不清,只能辨认出最后一句。
“......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为国家做贡献......死而未悔。”
面对记者,王孝礼平静地说道:“娃走了,我得接过他的担子,只有让村子发展更好,他在黄泉下才能瞑目。”
村口出现了一座碑。碑的旁边是涧源村的村标,重新用油漆刷过,朝气蓬勃。碑的后面是一截断开的庞大的树根,树根已没有任何生机,已经开始腐烂降解,但树根的周围却长出了一片野草,茂盛着,伸向天际。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碑上刻着“烈士王与义之墓”,背面刻着“落叶归根”。每天黄昏,总有一个佝偻腰身,两鬓斑白的老人轻轻站在墓前,轻轻抚摸着碑。




全部 0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