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纸婆》——第21届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省一等奖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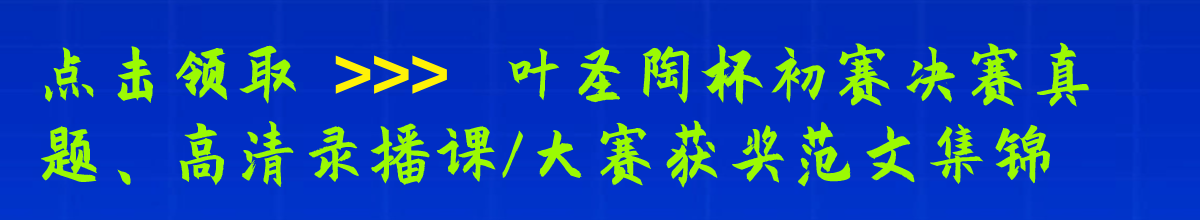
驶过弯弯绕绕的盘山公路,再走过两座渡河小桥,便能看见一棵高大的柳树,树下立着块石碑,上有“陈柳村”三字,“陈”是村姓,“柳”是村中多柳,在这里,我遇见了一位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陈纸婆”的婆婆。
那天,我正走在村里崭新的水泥路上,欣赏着家家户户门上、窗上美丽的剪纸,为它们的精巧而惊叹不已。
忽地,一抹跳跃的“红”吸引了我的注意。
那是一张折叠的红纸,在一双历经风霜的手中转动,翻转……红的纸屑如雪般落下,完美得被底下的小袋子收纳,红色的剪刀“咔嚓咔嚓”地不停扭动着,老人专注地看着手中的红色精灵,露出全然纯粹的笑容,而我却好像只能听见剪刀与纸合奏出的乐曲。终于,一曲终了,老人放下剪刀看向了我。
“小娃儿,你喜欢?”老人带着不算特别重的口音笑着问我。
我有些羞涩地抿了抿唇,一言不发地看着老人手里的剪纸。那是个好常见的样式,抱着大鱼的娃娃,朵朵莲花边上配字“连年有余”。若是平时,我必然扫一眼便漫不经心地略过,但这次不同,我亲眼见证了它的诞生,看它舒展四肢,抖下点点碎屑,从叠着的破碎红纸变成一副剪纸,一个精致的艺术品。
而现在,老人将它递到我手中。
看看手中的剪纸,又看看拿起另一张红纸像是要继续剪的老人,我忍不住开口,询问这村中剪纸是否都是她剪的。老人停了动作,带点讶异和怀念看向我,她点点头,而后重新开始剪纸。
伴着清脆的剪纸声,她缓缓向我讲述了一个故事。
当年的陈柳村还不像现在这样,那时盘山公路未修,渡河的桥塌了一半,唯有枯水期才能走个几十公里,到外边的小县城去。
村里都是黄泥地,一层的小平房有时还缺半截屋顶,村民们靠种田为生,农忙时脚不沾地,农闲时大家便喜欢聚在村中间那棵大柳树旁。而她喜欢蹲在树下,看村东那几个姑娘边聊天边剪纸,那闪亮亮的剪刀蝴蝶穿花般得上下翻飞,可给她羡慕坏了。于是没多久,她就忍不住找她妈要纸和剪刀了。
说到这,老人又看向我,她手中动作不停,边剪边笑呵呵地问我,让我猜猜看她的妈妈有没有给她纸和剪刀。
我略有迟疑地点了点头,却见老人脸上的笑意又重几分,她咧着嘴,露出缺了半个的门牙,大声反驳了我。
“不对!”
在她的母亲看来,剪纸这种东西只有那些有家传手艺的人才能剪好,而她想剪纸,那就是在浪费纸。纸都不给,更别提剪刀了。
没有纸也没有剪刀,可她就是想剪纸,那怎么办呢?她想了个主意,趁爸妈不注意时,偷偷拿一张留着过年时用的红纸,想剪纸时,就用磨的细细的炭在上边画,画要剪下的地方,就像它们真的被剪下来了一样。画完就努力把它们擦掉,这样就是张新的红纸了。
她就这样“剪”了很久,直到再也写不上去时,她才不得不放弃继续的想法。但也刚好,这张用了许久的纸可以变成真正的剪纸了。
又是趁爸妈不在的时候,她偷偷避开兄弟姊妹,摸走了柜子上放的剪刀。
剪法早已烂熟于心,但直到下剪的那刻,她才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平静,手在颤抖,心在激动,直到最后一剪落下,哪怕那副剪纸剪的再错漏百出,那满溢的快乐依旧让她到现在都记忆犹新,连第一次去县城时的快乐都比不过它。
而当她剪完三张剪纸时,仿佛上天恩赐一般,那几个在树下剪纸的姑娘发现了她,不,应该说是早便发现,只是现在才来找她罢了。
那些姑娘从柳树下起身,走到她面前,那叠渴慕已久的红纸就这样被递到了她手中。
姑娘们要结婚了,以后没什么精力再去弄剪纸什么的,于是就在嫁去外边前将这些不需要的红纸给她。
对她而言,这是天大的好事。
说着,老人的笑容淡了些许,她手上的动作放缓,语调也低沉起来。
那叠红纸她省了又省,勉勉强强坚持到她开始工作。
她工作的地方是县城里一个工厂,每天要天不亮从家半骑半推着自行车走几十公里,傍晚又从工厂回家走几十公里,大部分空闲时间花在了路上,可她还能找到剪纸的时间,只要缩短点吃饭或休息的时间,就能得到足以消除全部疲惫的快乐。
而她与她的丈夫就是因此而认识的。
老人只提到了一句她的丈夫,随后便开始讲其他东西。
后来我才从其他村民们那了解到,老人那个因纸结缘的丈夫,在某天晚上因为疲惫与才下过雨的湿滑路面,一个没稳住跌下山去,没救回来。
老人停了剪纸。她将纸轻轻展开,那是只展翅的凤凰,随着清风颤动着翅膀。
“我妈常说,要努力,到外边去,当个金凤凰,从这山沟沟里飞出去。”她将这张剪纸也递给了我,“现在变好了,上边修了路,不用想着当金凤凰才能飞出去了。”
老人眯着眼,满意地看着整洁美丽的陈柳村。
“外边的人喊我什么,剪纸艺术家?这名字真讲究。我还是喜欢他们叫我‘陈纸婆’。”她轻轻叹了口气,“我就喜欢捣鼓这纸,没想到这一捣鼓就是一辈子了。”
不久,返程的时候到了,我坐上车,反复地看了看陈柳村,那镶嵌在绿柳萦绕之中星星点点的“红”,伴着发动机的嗡鸣声渐行渐远。
我离开了陈柳村,带着老人剪的纸凤凰。





全部 0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