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少年班,一场45年的天才教育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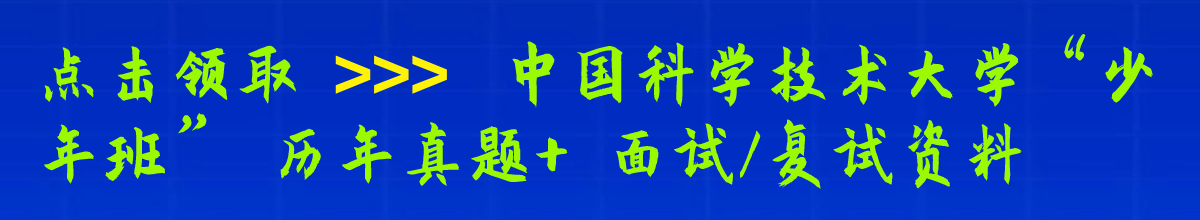

 2008年9月2日,13岁的张炘炀以“年龄最小的硕士研究生”身份考入北京工业大学,在父母的陪伴下来学校报到。
2008年9月2日,13岁的张炘炀以“年龄最小的硕士研究生”身份考入北京工业大学,在父母的陪伴下来学校报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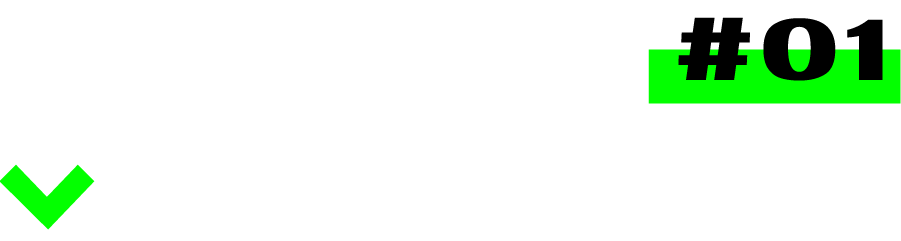

 中科大少年班学院学生宿舍。
中科大少年班学院学生宿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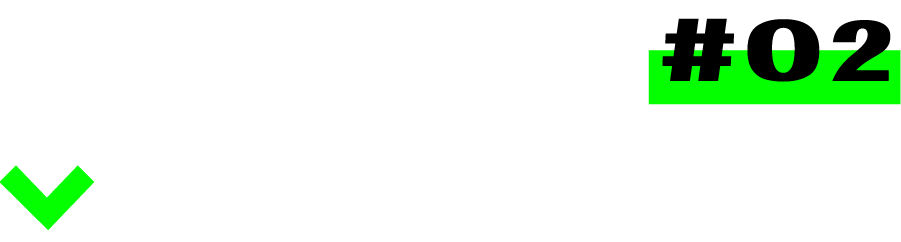
“他们只是很聪明”

 2017年6月11日,安徽合肥,中科大少年班创新试点二班拍摄毕业合影。
2017年6月11日,安徽合肥,中科大少年班创新试点二班拍摄毕业合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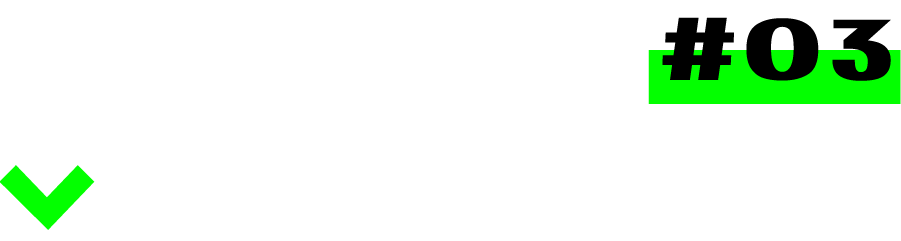 “我后悔读少年班”
“我后悔读少年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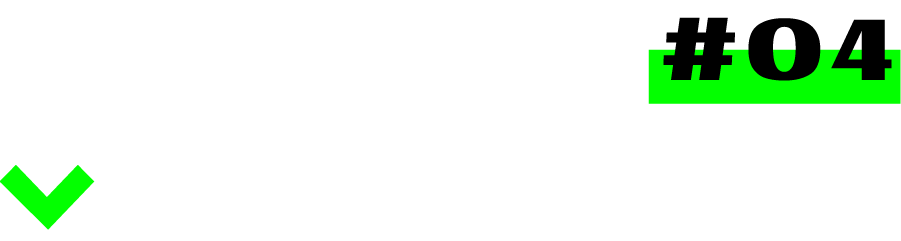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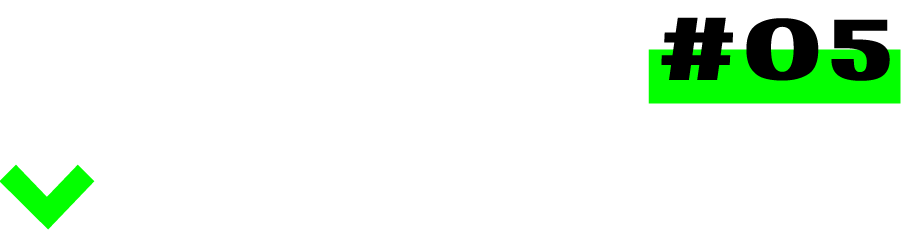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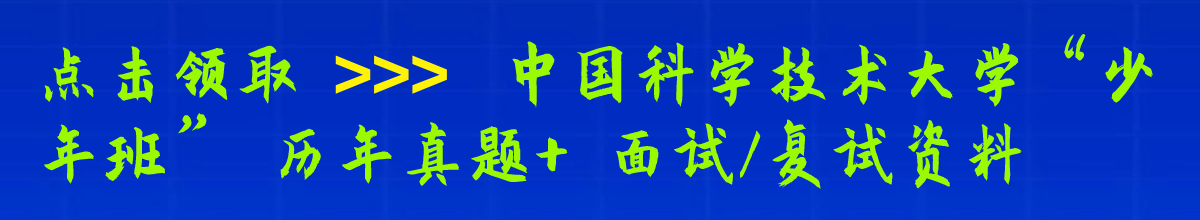

 2008年9月2日,13岁的张炘炀以“年龄最小的硕士研究生”身份考入北京工业大学,在父母的陪伴下来学校报到。
2008年9月2日,13岁的张炘炀以“年龄最小的硕士研究生”身份考入北京工业大学,在父母的陪伴下来学校报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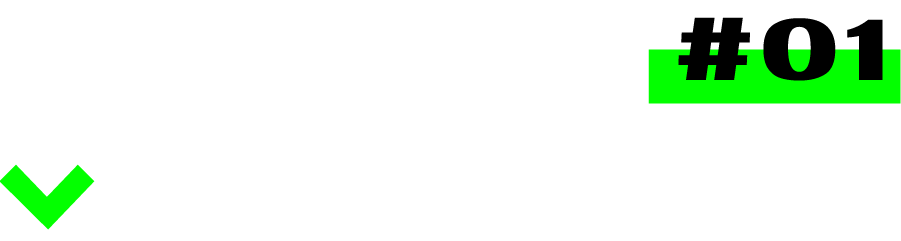

 中科大少年班学院学生宿舍。
中科大少年班学院学生宿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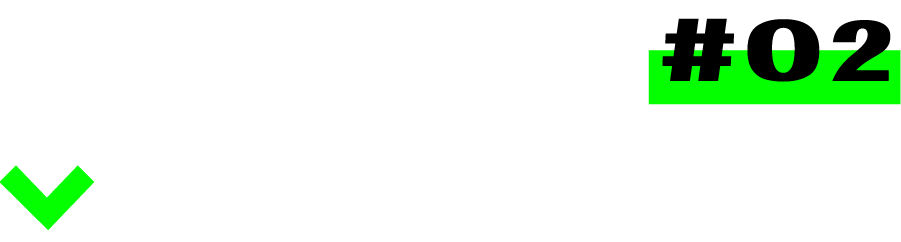
“他们只是很聪明”

 2017年6月11日,安徽合肥,中科大少年班创新试点二班拍摄毕业合影。
2017年6月11日,安徽合肥,中科大少年班创新试点二班拍摄毕业合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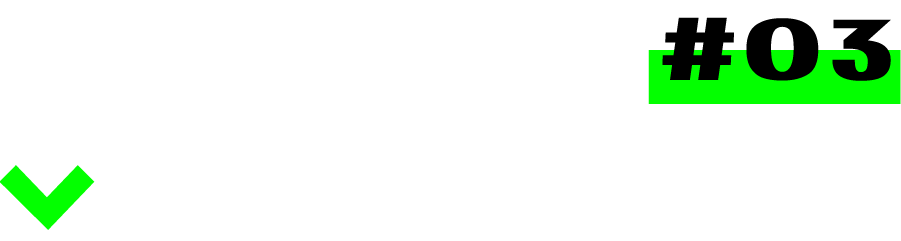 “我后悔读少年班”
“我后悔读少年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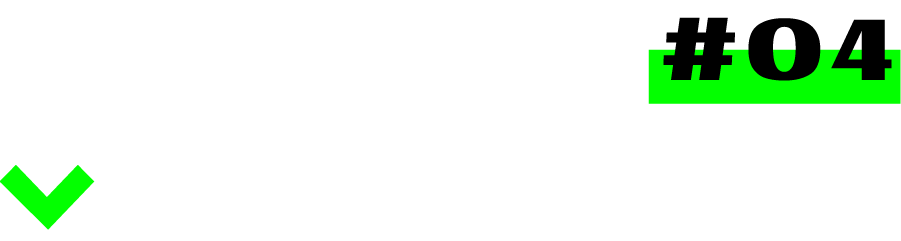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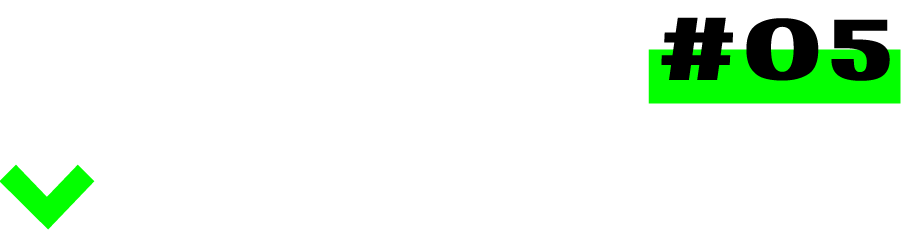

发布于 2024-04-13 17:54
全部 0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