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眺(第十九届“叶圣陶杯”初赛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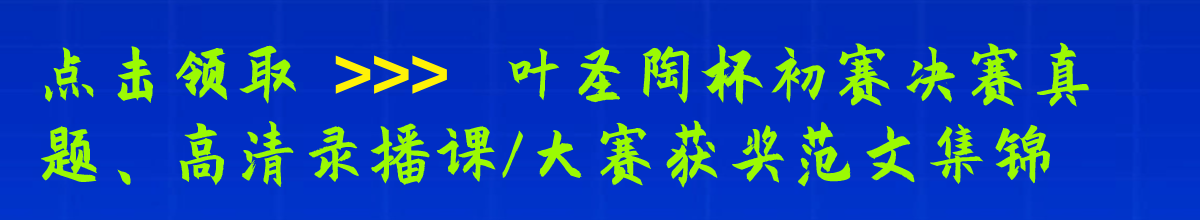
指导教师:舒沛
我竭尽所能向你描述我的家乡。我用我的声带发出声音,汇成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有渊源的语言;我用手臂挥舞,拟作掠过天穹的群雁,你却感到模糊。你摇头,我们跌坐到草地上。我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最后,我托起你的下巴,你面朝夕阳。
“就像那里。”我的目光顺着指尖延伸。就是这样。明明并不附庸于任何宗教,她却给予我神迹一般的神圣,令我身处其中时感到荣幸,被剥离后则留下虔诚。在很遥远的某处,蜿蜒的溪径身侧,伫立着灰蓝色的岩石,从容地击打着韵律。水流则是丛林清脆的歌喉,轻盈地抹去了山坡的棱角。四季从山坡上滑下来,从此,流淌向人间。
道路是棕红,金黄与墨绿的。鞋子的颜色则更多。可是踏上去却格格不入了,但没有人走,如何叫做道路呢?不知来自何处的源泉,散布下巴掌大的水坑。亦如繁星点点,每步行一次走神的间隔,就又能发现一潭。这样的路很长,并且越走越窄,那是因为两侧的东西越来越多,它们中大抵是有生命的,于是乎都在往外面探去。它们或是没长出明确的双眼,但它们确实能感受到些什么。来的人,走的人,来了又走的人,再也没回来的人。而一路上都是有小溪的。年幼的草木像顽皮的孩子把根须扎到水中,河流则宠溺地舍弃了冰期,换来了一年到头的欢声笑语。不过是,只有生长在这里的东西能够听闻罢了。这片土地,人与山,山与水,水与天空,这里面还藏了多少家伙,要过了桥才知道。
桥有两座,一座卡在溪径与水库中间,他是守护身后这片圣域的战士。他宽大,深沉,棱角分明。若不是见他热情似火,便是感到冷若冰霜,毕竟我只于寒暑假与这位长辈相会。他不拘言笑,却分明让人亲切;他朴实破旧,也依然威严。他从来面向外界,我来时与他迎面,他显露出怀念与欢迎;我走时背对着他,那灼灼的目光是哀伤,对我们是否还回来的怀疑,还有对以.上两种情绪的克制。他是一座忠诚勇敢的桥。他有着惊人的年纪,却从不以垂垂老矣之势出现。他顶天立地,用双肩同时扛起了游人思念家乡的情怀,和父母对孩子的担忧与爱。
另一座桥在道路尽头。对于一路野性斑驳的自然,这座桥通向方圆百里唯一的人文痕迹。相比,她便显得温柔极了。只是,她也分外固执,这撑起她坚不可摧的脊梁。可是她又如此脆弱,铁红与风化锈蚀着她的栏杆,哪怕只是风经过,她也颤颤巍巍地,保持着平衡,护送我回家。她打理着这片空间,把疯狂的灌木,野生动物,竹林和荆棘拒之门外。她硬朗,不屈,挺拔,也俊俏,在她年轻时。她的路面是石英的白,栏杆是斑鸠的褐。她也许远离时代与世尘,可她也决意向她的家人们--我,我们,展露出战士的模样。她也老去了,可她却努力着融入一年又一年变化着的我们。因为自进入山间,我们必须日夜相处。如果她不似现在这般开朗,我们之间就不再自然了。
还有井,他离家很远。但水桶会载着水回来,不过,一次比一次晚,时间一回比一回短...她似乎有些忘本,可恶的是,还在违心地讲:想念。可是她总想着,大家都远离溪流,随她到人们把石头从山上敲下来并垒起来的地区。她运作,卖力,受伤并为自己的价值而高兴。这是她在这里不曾能体会的,我想。可是这里有人爱着她。我们都是,但我们不舍得让她受苦受累,于是护她在温室里。但她总是向外眺望。水桶爱着井,不过不胜爱我们。于是她总是外出,但也归来。
可是,风和草木都在呼唤我们啊。道路两侧的生灵都在等待我们呢。他们许久没感受到归来的人了,他们也许欢笑等闲,可他们也在为我们的离别而心寒呐。
当下啊,家乡空余两座桥,一条路。
点
评
家乡,是游子摩挲多年的圣地,是永远怀念的远方。作者以游子的眼光回顾了家乡的山水、桥、井……和年迈的长辈。以“两座桥”寓指朴实深沉的外公,硬朗温柔的外婆,以“井”看似责怪“背离”家乡的游子,但不难看出被现实所迫而不得不离开家乡的无奈和对家乡的深切怀念。全文感情真挚,语言优美,其中不乏反思和思考,故为一篇佳作。
指导老师:舒沛
个人简介

从小是自森林、田野、与溪流的交汇长大,拥有一个孤独而丰满的家乡,后在南京进行义务教育,对家乡思念渐浓,也学到许多赞美家乡的语言,从此,“家乡”变成了一个希望的载体,精神的家园。现就读于南京十二中,热爱语文学习,兴趣爱好广泛。
获奖感言
我一直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方向,因为在前行嘛,漫无目的毕竟不好,我的方向就是“家乡”。一次我和我妈在仙林湖公园散步,她说这是算“郊外”,我说不算,算是“户外”,她就问“那你老家算郊外吗”我说也不算,那是“世外”。我家乡是与众不同的,是不愿分享出来的,但我想让诸位羡慕羡慕,所以我写它,同时敛它,藏纳它,在我的语言中,也在我心中。当我用语言包裹住这样的瑰物,它就令我放心多了。渐渐的,我所向“家乡”前行,也并非那个我每个假期能回到的家乡,而是那个受我珍藏的过去或未来,擦肩而过或遥不可及的家乡。但我终将实现它,用我的执念与胆量。




全部 0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