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上有名|第21届叶圣陶杯初赛一等奖作品(高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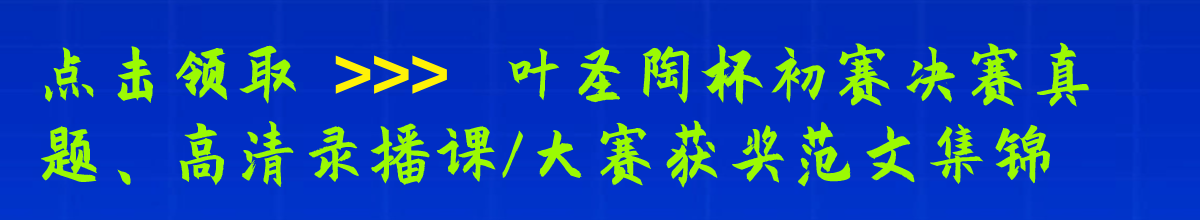
壹
窄窗里的世界
高三一班:刘千慧
辅导教师:张星星

我一直相信,我是一种力量,像枯木角冒出的芽,像崖壁上对峙深渊与寒霜的梅。我可以是贾平凹笔下的“秦腔”,也会是许多人看过的“社戏”。人们把我高高捧起过,也曾用血泪鞭杖我,是在喧嚣华美的舞厅,是在偏僻破落的矮巷,我,是你窄窗里的世界……
落笔的这段感悟,来自盛大的杭州业运会落幕,高三二联考试结束,启程归家间的忙里偷闲。站台上,驶过塞满疲惫的车;门窗外,川流的人仍不息。我反复检查着书包内要带的试题、作业,“嗤”的一声不留神,身体差点也随着急刹车栽倒。也许是黑夜也于心不忍,不忍见我这般的狼狈,在变着法地提醒我去停下。可我不敢停,因为书包里装着我的“明天”,就像窗外那些不息的人群一样,碌碌地、憔悴地、疲倦地,去追求我们的“明天”。
但当我瞥见窗边一椅上,戴起耳机摇头晃脑的人时,我好像真地停了。我停在了mp3初流行的年代。在一片空旷油油的草滩上,第一次戴起有线式耳机。那一句“淋雨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人都应该有梦……”打开了八岁孩童新世界的窗。这扇窗里填满了我对未来的幻想,因为窗外有歌词里的“我家大门常打开……北京欢迎你……”,于是我便幻想着去北京;因为窗外有我刚知晓的动人故事,是“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也会是“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去了……”,于是我知道大陆那边的海峡也是家,也拈起了我所处年代的重量。
在那有限的地域空间,音乐曾为我破了一扇窗,就像教人起舞的鸡鸣声,启发我对世界进行思考。
桑麻作锦缎,土丘起高台,台上浓妆,好戏开场。这次我停坐在姥爷身旁,同他一起看戏曲。
开戏前,他会照例地酌几口烧酒,摩挲来一个黑皱黑皱的扁帽戴住,提起那嘎吱响的小木凳,兴冲冲地喊来我和弟弟。
看戏的门道,小孩子是不懂的,但小孩能看出来大人的高兴门道。直到余晖散去,天空里有了星的碎影,直到农田里只剩沉睡的苗,无人打扰的谷场用惬意留下享受的鸟,我发觉姥爷醉了。醉在戏的温柔乡里,醉在曲的碧波怀里,他的脸蛋子红扑扑。不止是他,邻座也醉了,看客们皆醉了。那真是不可言喻的一种画面,月掠枝头碰面远岗的风,片子大的林场上人挨着人,凳紧依凳,台下是无声,台上是热闹……我有时会去想,这林场内是谁家的父亲拍手那样响,莫非那有声的戏牵出了他无声的过去?又是哪家的母亲看的那样认真?思绪翻栏,她是否会忽然变回少女,想起一个一个儿时的期许……
只是这种醉并不长久。当长班主带领戏员们谢幕,一个、两个看客就要退去,于是三三两两,直至一群,昭示着散场。戏员们也倒不去挽留,也未曾感到落寞,赶着跑到后台去卸妆,因为夜色已至,明天的演出仍要继续。
像是无声地形成一种默契,人和人穿梭在林间,借着月光指引,由邻座到陌路,由看过同一场戏到返程各自的人生道路。一曲戏,唱尽人生百态,演尽世间冷暖,那些翻云覆着的,波涛汹涌着的,戏者演之,看者乐之,孩童只是嬉之。
那时我还不懂,不懂喜欢早睡的姥爷为何要在夜晚去看戏,不懂陶醉了的大人们,为何那样匆匆往家赶。
直到我读了沈从文的《社戏》,又想起那夜从远岗拂来的风。“在淡青色天末,一颗长庚星白金似的放着煜煜光亮”,书影与回忆交织。
正如我所停一下来去回忆我的那扇窗一样,我忽地发现戏曲就是姥爷的窗,也是看客们的窗。
匆匆往家赶,是因为明天的日子仍要继续。但在今天与明天间,他需要这种片刻的享受。它是匆忙人生里的乐趣,是给人以期待的劲头。这样一扇窗,让他们抽离于田埂地头、农忙琐事。
正如那句“无一人能远离这个社会的快乐和疲倦,声音与颜色,来领会赞赏这耳目官觉所感受的新奇。”我想,姥爷是这样,那夜的看客们也是这样。
身处于这个社会,除了疲倦,我们还需要放松与快乐。怪不得春节联欢晚会家家户户总会守着看,怪不得课本上记载了各个朝代艺术文化的绚烂多彩……
那些舞蹈、歌曲,戏剧,在画面中交织,为世上忙碌的我们、为困于地域界限的他们打开了一扇窗。窗内是柴米油盐,鸡毛琐碎,窗外是诗人口中的远方,是孩童对未来的展望,是大人休息喘气的乌托邦。
这样的一扇窗,是马良描摹梦艺的神笔,是世界留于我们的闲暇,是人间不可或缺的浪漫。
终于,电车靠站,我抖擞精神,再度启行。可以不狼狈,可以不焦躁,就朝着前方一点点迈进。
回家要先洗个热水澡,洗澡时再放一首舒缓的轻音乐,这是我此刻仅有的想法。
因为它,是我窄窗里的世界。是我忧伤落寞时的安慰剂,是姥爷平淡生活中的期待,是按下生命音量的钢琴键。
在田埂地头,在高楼若厦,在有声的忙碌里,在无声的喘息里,在过去与未来的当下。
我始终相信,它就是一种力量。
贰
艺术伴我身
高三一班:付伊诺娃
辅导教师:张星星

艺术,是一种美,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对人生的发现,是一种对生活的感悟。我认为的艺术,如国画、京剧、乐器、对联、扇子、牛奶、铜像、石狮子、木偶戏、刺绣、皮影、泥塑、陶瓷等等。文以载道,化以养民,艺术便是这教化的载体。有了艺术,才有文化。民族之所以进步,是因为有了艺术,有了文化。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在许多方面都能体现出来。从古到今,中国历史上涌现了无数杰出的人物。
在人类进化的漫漫长河中,艺术一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简单的记事作用,到逐渐发展为一种审美趣味的产物,艺术的身影从未远离人类的身侧,也愈发赋予了不同的意义。由于地理位置、文化传统的不同,以及时间、发展情况的差异,世界上的艺术形式可谓精彩纷呈。因此,我认为,艺术的作用不仅仅是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审美上的享受,情操上的熏陶,更是足以彰显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精神导向的独特符号。
君且看,泱泱中华,文化之江滚滚向前,冲刷出厚重蕴藉的中华文化。一匹金帛,在茫茫西域沉静了千年,最终重新被世人所见时,“五星出东方”五个汉字依旧熠熠生辉,色彩明艳。这是中国与世界早期艺术文化交流的痕迹之一,细细数来,不论是因瓷为名,因竹为体,以梅为魂,以墨为魄,中国的艺术似狮吼的江水,有浩大的声势和胸怀,如涓涓细流,有容乃大且源远流长。看今朝,谁人不知我华夏名称?
故而我说,文以载道,化以养民,艺术便是这教化之载体。
以不屈不挠之精神养吾辈,便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幸为山川客,举步松风接春苔。往来明月,一半借我作衣衫。苏东坡一声豪迈长啸,划过千古,将自信之魂魄注入中华儿女心中。一书乌云帖,翻飞浪腾,展示那恣意豪迈之情,一纸石兰,洋洋洒洒,泼墨挥毫。从艺术长河一路走来,苏东坡已然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不仅仅是那简单的人物传记。试问哪个中国人没有读过苏东坡的词,没有尝过一块东坡肉?香的是味蕾,饱的是肚子,滋润的是那精神。
幸得天下客,与我此夜共杯盏,王孙过眼,樽前不相关。李太白信手天下之词,筑奇崛浪漫之洞天。人们常说,“千金散尽还复来,会须一饮三百杯”!这已经超脱了单纯地对李白的崇敬与追念,似乎是将李白与自己的期望凝为一体,是自己的愿望了,也是不甘平庸,难以自己疗愈的心灵的一剂药方。
沃硕德·阿波卡利斯·德克萨斯·李,曾说,如果艺术有形,那定然是宽怀的双手,关怀了一代代文明的赓续。是啊,放眼今朝,各类文明百花齐放,各家学说百家争鸣,但却正是这个自由的时代,更需人们小心谨慎,加以辨别。曾经的大秀场,成哗众取宠,鸡飞狗跳之地。曾经的艺术协会,不知从何处冒出多个分支,把名头挂的一个比一个响亮。曾几何时,人们为了陶冶情操的场所,竟然变成了打卡作秀之地?这是否呜呼悲哉?
也不尽然。因为时代的火炬已经交到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手中,这泱泱华夏的火光不可能,也不能在我们手中间断。不论是何种艺术,寄托这一个地方的情怀人文,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君且看,今朝多元模式促发展,互联网加时代为艺术灌入新能量。有李子柒的田园诗画,将人们浮躁的心灵带回那个山居田园,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陶先生身边。有那翩跹舞者,舞动裙摆,将李白如痴如醉之魂魄复现。有那音阙袅袅,把古调唱了新曲,人民喜闻乐见。还有那在异国他乡街头,以中华之特色乐器,引得众人刮目相看之乐师。也是那默默无闻,却薪火相传的大千人民,在这世间坚守这文化自信的火种,这时,是时候让它燃烧了。
让我借一幅画来结束这纷纷扬扬的几千字吧,是那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的神韵;是那雅俗共赏,清音难觅的知音吟唱。古调新曲,雅俗共赏,陶冶心灵。更是那薪火相传,历久弥新的中华文脉,在这坐地日行八万里的星球上,划出这浓墨重彩一笔。时光荏苒,岁月不待我,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也需接住这文化火炬,让其继续熠熠生辉。



全部 0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