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届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获奖作品展示(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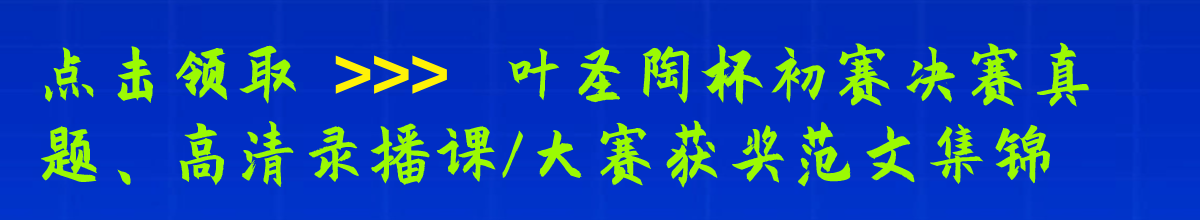

高一5班 张楚妍

<<<<
《恰似飞鸿踏雪泥》
虽千百年已过,仍愿你眉上风止。
——题记
遥望天际,有小亭伫立。天边云彩与青山融成一线,照亮了西湖上的半边天。
从这里一直向南就走到了。它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似乎每次总是卡在那正正好好的位置,不偏不倚,无声无息,也就终于迎来了他。
曾看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脊梁自古以来就有......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以前的他,生动鲜活地存在于朝堂之上、百姓心头,才华横溢至如此夺人眼目。其人“犹如李太白再临人世”,其诗“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哪怕是辗转于各地,也仍可以肆意洒脱,毫不在意外界杂乱的声音。
直到响起了乌鸦的叫声。
“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百口莫辩,第一次体会到千夫所指,第一次遇到恶,所以他笨嘴拙舌,失去了反驳的力量。招了吧,招了吧,不招就要打,不招就要胡编乱造,不招就要硬生生给你安一个“造反”的罪名。
于是只能承认。
他心里清楚,承认便死期将至了,甚而至于写下了遗书。但或许上天偏爱才华横溢的文人,百姓们向前一步,王安石上书劝帝,太后求情。奄奄一息的太后死前对皇帝说:“我记得苏东坡兄弟二人中进士时,先帝很高兴,曾对家人说,他为子孙物色到两个宰相之才。”“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罪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这些话道明了某些真相,我却一直百思不得其解,既是早就发现其有宰相之才,事情又为何会到这般田地?到底哪里脱离了正轨呢?
大概是世道人心吧!世道偏了轨,人心变了质。
宋神宗终于还是没说什么,将苏轼贬至黄州。
就此,乌台诗案正式了结。他自御史台处缓缓地走出,似乎容颜未变,却有某种更坚实的东西突兀地显现在他身上,覆盖了以前的欢声笑语。
说完这个沉重的话题,来看看苏轼的生活吧。抛开别的不说,苏轼的多边性真的让人拍案叫绝。他可以是在面对妻子的离世时深情的丈夫,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可以是“热衷酿酒的内行中的外行”,有“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可以是美食家,有“东坡肉”流传于世;可以是画家,有《潇湘竹石图》......
似乎他的形象不再在空中漂浮着看不真切了。
他可以是才华横溢的,可以有大家风范,但在我眼里,他似乎更洒脱,更具有孩子气,更关注民生,更像“中国脊梁”。而中国脊梁像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存在于人的躯壳中,只有在某个非常时刻,你才能清晰地感觉到。
而苏轼就是这样的人。哪怕他再“多边”,才华与书卷气再交织,也抵挡不住那“筋骨”的傲然挺立。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又回到了西湖的小亭上。他将美景比作美人,成就了千古名句,也留给了后人无限的遐思。然今人却不知,当时的西湖,湖水将要枯竭,枯竭就意味着杭州将会变成一座废城。就在这时,它再一次迎来了苏东坡。他由诗人摇身一变,成了一位水利工程师。
“诗人的职责是描写美女将死时的凄艳,而苏东坡则想救她。因此,他宁可不做诗人,也要做个真正的男人。”
于是他上奏朝廷,多方汇集工程款项,制定周密的计划......为纾解心中愤懑,为拯救民生,为保护美丽城市,为稳住国家大势。凡此种种,成就了今天的西湖。
最后的苏东坡,应该是平静的。人到暮年终将趋于平静,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他人的平静,带着死气沉沉的气息。但他的平静,更像是对自己的肯定,对生活的冷静。不再像个少年一样莽撞的奔跑,遇到挫折爬起来后还能露出开心的微笑。
或许是被岁月吞噬了棱角吧。但我总觉得有另一种更加坚韧的东西破土而出。
纵观他的一生,不是风流如李白,不是怡然如陶渊明,不是豪情如辛弃疾。这位大文豪在我的眼里,更像是过着老百姓的生活:有磨难有欢笑,有悲伤有喜乐。也曾有过“高光时刻”,也曾无限靠近过生命的边缘。但正是这些经历才成就了他,正是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在看他的时候眼前不再蒙着厚厚的历史幕布,而是无比清晰,也无比震撼。
他身上承载着历史的重量,但我相信他更愿意卸下这些重担,去研究诗文也好,书画也好,吃食也好,酒饮也好。这些一点点地呈现在他的人生中,使其潇潇而立于人世间,潇潇而立于中国的历史上,撑起了宋朝的一方天地。
再次回望西湖,或许这只是他人生的一个站点,我却站在这里驻足,回望了苏轼坎坷的一生,久久无法释怀。
就像《活着》中告诉我们的,旁观者或许有无限悲痛,但代入到书中的人物中去,以他们的角度去看,又有那么多幸福美好的回忆,像走马灯一样,历历在目。
所以不必为苏轼而悲,亦不必为他而喜。他像飞鸿踏过雪泥,在历史上留下点点微痕,即使只是在漫漫星河中的一瞬。
但多么庆幸,我们见过,我们记得。



全部 0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