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杯”作文大赛优秀作品选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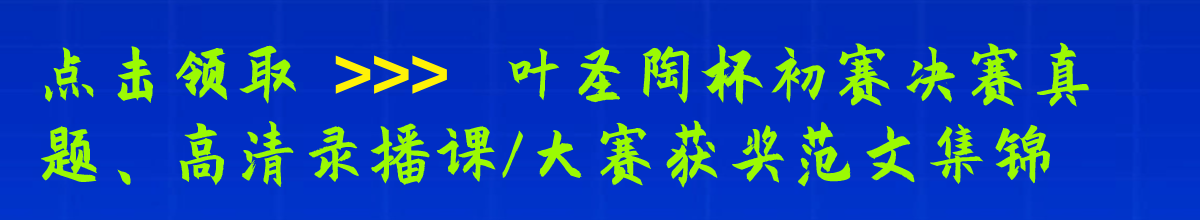
青色大门
(初赛一等奖)
高2018级4班 罗圣平
旧说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诸者,每年八月浮槎往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博物志》
我常在梦中拜访一扇青色大门,自下而上滞留些历史的痕迹,粗鲁的脚印,缺失的木料,姜黄色的铁锈,模糊的门眼。梦里的一切都缺少时间概念,所以梦醒后很难区分梦中的人和事,只剩某种意象的存在在现实中再进行编织重组,形成完美的梦。
门边有着许多杂乱叠放的花盆,让我想起小时候爷爷家的阳台上也有着许多同样朴素的花盆栽种着仙人掌、喇叭花这类不起眼的植株。这些花草被爷爷视为宝贝。小学放学后我就爱跪在沙发上虔诚地望着那片灰绿色的植物。“平平,你看那盆仙人球又开花了,黄色的,看到没。”“那盆又长了个小包出来春天了,你看那个喇叭花要开了"我总是习惯性的以哇来回应爷爷表示我的欣喜。现在想来,一盆植物的生长需要以哇这样的惊喜来对待是否会稍显幼稚与愚蠢,不过当时的我又确是爱着那片绿色小天地的,以至于长大后的我仍习惯于为一朵花蕾而感动。爷爷待它们同自己的孩子般,每天一遍遍的浇水,不厌其烦,直到搬家。家里的大人早想把爷爷那一屋子的破烂给扔掉,爷爷耳朵不好,性格固执。所以搬家那几天家里的争吵不断,只听到爷爷不断提高嗓门喊着我“我要留到,你们谁也不许给我扔!“我无从参与大人们的决策,只能呆呆望着那几盆仙人掌。不过大人们的行径在我看来却颇有些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意味。
其实大人们口中的破烂都是我的宝贝。爷爷的房间本不小,不过堆着许多一摞摞保存好的书籍报刊,各式家电的包装盒,陈旧的柜子,铁质的储物架堆满了锈和爷爷到处旅游淘来的鹅卵石。在这些别人看来杂乱无用的东西里,我却能找到我的宝物。爷爷有个上世纪邮政局的绿色军包,样式古旧,里面装着的是哥哥们玩剩下的玩具,比如红色大字写着的上海玩具制造厂生产的跳跳棋(搬家后我依旧保留着)各式的拼块模型,片片撑起我那段美好的童年记忆。我永远记得那天,爷爷终于打开他那神秘的白色柜子,拿出册册邮票集给我看。那些邮票按时间顺序进行整理,我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他们,花花绿绿的图片代表着这么多的历史,尘封在一张张邮票里又尘封在爷爷每一册认真整理的书籍报刊中。爷爷喜欢在餐桌上整理报纸,俯伏于案前,昏黄的台灯下爷爷拿着小刀仔细的裁切着一张张报纸,用笔写着些什么,那些裁下来的新闻就放在餐桌里的抽屉里。我学会写字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好奇爷爷的字是怎样的,不过这种好奇心终因学业的繁忙搁置。直到那天我的生日爷爷在红包上笔力遒劲地写着几个大字,祝福,平平生日快乐。
总之,直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许多在那座城市里少有的破旧楼房里发生的故事,从一楼爬到二楼一共有十节阶梯,冲到爷爷奶奶家最快的方式是一次跨三阶,拉开那扇贴着倒福的铁门,再敲敲里面的门就能迎上奶奶惊喜的脸,爷爷“我又买了糕点要不要来吃”诸如此类的问候。厨房常有着蚁患,为此爷爷想过许多办法来治。那口用了几十年的铁锅奶奶常用作给我焖胡萝卜饭,很甜。胡萝卜的清甜沁进米粒,沁进我长大后的梦。奶奶也爱给我烧肘子,混着颗颗精挑细选后的黄豆,一个很小的烧锅,米白色嵌着好看的深褐色。奶奶很厉害,会自己做凉面,因为那碗自己做的凉面,我总是期盼着夏天的到来,面条倒入锅中,漾起一层层白雾,捞起来晾干,开着风扇和奶奶一起等待的时光,我和奶奶都偏爱豆芽,爱在凉面底下铺上厚厚一层豆芽,吃起来清脆爽口。不过,在我花更少的时间冲上爷爷奶奶家大门的时候,他们却在花更多的时间费力的爬上那不过五层的楼梯,顺带着上来的还有爷爷沉重的轮椅,奶奶模糊的视野。在我还未察觉的时候,那段最美好的回忆就已经停留在五楼,我却再无力爬上。
搬家那天,我执意要留下爷爷奶奶的一些书,其中有一本是奶奶年轻时的工作笔记。正红色的封面上画着人民解放纪念碑,密密麻麻记录着化学实验的注意事项,里面还夹着那时的信封、出差证明、八四年的选民证。纸张已经褪色,甚至有些脆弱,我小心翼翼地收藏这个本子,仿佛是一件文物般。
搬家那年,我考上了高中。我以为我会继续前途光明,爷爷奶奶也陪伴着我继续过着平凡幸福的生活。可时间却在不断提醒我,他们老了。
没了可爱的绿色仙人掌,大人们总嫌那仙人掌多刺会扎着手,不如干花来的好看利落,还不需浇水,不怕枯萎。焖胡萝卜饭的味道永远停留在记忆里,奶奶手忙脚乱地炒一道菜却伴着生。家庭聚会时,他们总是带着满脸的笑意,静静看着我们说笑,因为他们听不见,无法参与我们的讨论。
从低矮楼房搬到电梯公寓,从陈旧的房屋到宽敞明亮的大客厅,从走路到现在微信联系,他们总是在等待我们的消息。
没了幼时的乐园,我的生活似乎也变得黯淡。我的高中生活不算糟糕,结识了许多朋友,学到许多知识,可总归难免渗进一些委屈痛苦。小时候哭总会威胁我妈再打我我就去奶奶家,那时我家离奶奶不过几条街道的距离,可我却没有去。搬家后他们就在我家楼下。那天我终于实现我小时候的愿望,可我不想让他们伤心,我就躲厕所哭。可是耳朵并不好的奶奶却能感应到我的抽泣。从那以后我使发誓再也不去爷爷奶奶家哭。
老人和小孩是一类人,我总是这么认为的。那天父母出差,我去奶奶家睡,因为第二天早上急着上课便走的很早给奶奶留了张纸条,说我睡得很好,谢谢奶奶。结果那天回到家中妈妈告诉我奶奶看到纸条哭了,原来奶奶也是同我般感性的人,去卧室一看奶奶还把我睡觉抱的小熊端正的放在枕头上,煞是可爱。
这些事物意象的叠加,在我心里变成回不去的梦。在噩梦里惊醒,才发现泪水哭湿了枕头。
我开始变得愈发紧张,紧张于那些时间节点的到来,半期、期未、成人、高考、大学。城市的样貌一轮又一轮变着,往往街道这一边的工程才完工另一头便跟着开始了。夜晚变得热闹而迷人,灯光下的人们细数着白日留下的遗憾,氤氲对未来的渴望期待。我开始漫无目的穿梭在一列列地铁,一条条人行道下,偶尔仍能看到熟悉的青石板路,但看见那不断重修的旧楼表面,已是物是人非。
我像是做了一场大梦,大梦初醒后我在回忆的怀中,尽情留恋关于青色大门,关于回不去的许多日子。我仿佛能够听到那快要腐朽的大门嘎吱嘎吱地冲破时间束缚再次向我打开,可是我再也无法进入。我渴望乘槎而去,去向那最遥远的远方。
看见荒凉
(初赛一等奖)
高2019级3班 张之念
十二岁那年,在青海的大草原上看见两匹马和骑在马上的蒙族人。
马毛很长,马背上只垫了几块布,脸颊晒成黑红色的人在鞍上展翅。“那是儿子马,要参加那达慕的好马。”旅店老板告诉道。转眼那两匹马便劲风般地掠去,高大得让人瞠目结舌,马腿上块状肌肉紧绷,腿筋根根绽出,马蹄在空中腾起,马搅起草籽和土粒。马上的女人衣着平常,但只一眼,便知道那是腾格里的女儿。他们狂放地飞奔而去,向着不远的青海湖。那里的草滩被波粼搅得破碎,从水湾和草丘脚下延伸出去,蔓延成斑驳不平的深绿,长草尖端泛黄,蓬乱地耸出,又铺展成远方颠簸的原野。
那是很神奇的一番体悟,我永远记得草原如血的火红日落,粗犷的色彩泼洒在无尽的穹顶,整个世界只剩下荒凉的地平线,那里有几个遥远的山包,只听见劲风收刮着大片草原,像是暖风不曾吹去过的天边外。
这样懵懂的震撼一直延续到长大后,直到在蒋勋先生的作品里拣到这样一个词:世纪末美学。
那时的我惊醒:就算生活再怎样饱满,人都是需要荒凉的啊。
人类文明总是在有限中寻求和永恒的联系。生命永远有限,这就是每个生灵注定悲剧的一面,而对于亘古不变的向往和渴求,就总是带有盛大而悲凉的美感。世纪末美学,便诞生于这样无助又无畏的荒芜感。
更小一些的时候,在大连的轮渡上陶醉于色调暗沉的大海。北方的海同南方的海不同,没有了明丽和灵动,多了满怀磅礴的厚重凝瑟,我会无由地敬畏,屏息凝神地望着无边的灰蓝色铺展,排开。
就算是现在,回忆起来仍会由衷喟叹。是了,这样的美总比明亮的美更能把人引向深沉的思索,你会突然安静下来,感觉到自己的血液往人类起源流动,那个起点又像是终点,剥去一切粉饰,留下最本源最粗放的灵魂。
《红与黑》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很喜欢,写在于连的最后一夜,“这脑袋里,从没像在降落之际那么充满诗意”。于连,一个卢梭精神的典型,或者说是注定的悲剧,在奋力往上爬的最后一步,蓦然回到了最本真的自己,重新充满圣洁和诗意。
生命即将一片荒芜,生命即将漫天洁白。
似乎伟大的作家,都能在描写死亡的时候多出一番味道。雨果在《悲惨世界》里写安灼拉富有神圣感的离去,又讲“他入睡,我长眠。同是梦中人,正好相依伴”。优秀的艺术家也是如此。我最喜欢的一部音乐剧的末尾,已经离开人世的绝症少年有一句很美的唱词“望着漫天的繁星,拥抱这黑夜”。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中有一点相同——他们走向佛国或是天堂,都是走进无限。相伴的梦中人,怀抱星和夜,最荒凉的终点恰恰又是最幼稚而明净的起点。
我爱石黑一雄口中“父亲是很低的夕阳”;爱边塞诗一句落日长河,坐标轴一般至简的荒芜;爱张晓风在中国海滩上拣着愁乡石的眺望;爱曹雪芹笔下一袭大红斗篷和茫茫雪原;爱李煜舟中寂静的沉默;爱不知见证了多少荣辱存亡的石头城,又醉心于紫禁城朱红色的宫墙……
胡适先生写过,中国哲学的课题就是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找和永恒的联系。我想,年仅二十余岁的先生能写下这些文字,便也不难解释他为什么可以成为极少见的既卓越又极尽纯粹的学者了。
那些寂寞,通透,没落,都像是一个人,一段时光和历史文明的交点坐标,通向很久很久之前的故事,也通向没有界线的远方。
青海草原上有一段极美的高速公路,是那年我们因为错路而发现的。铺天盖地的草原直接从透蓝的天空里倾出,山坡上撒着零落的羊群,牦牛们慢悠悠地横穿过公路,肥硕的獭子高高地冒出一串圆脑袋。妈妈轻声说,我们好像走到世界的尽头了。
真希望每个人都能有这样一次经历,能有那么一瞬间站在你的世界尽头,看见一切结束,然后生命的齿轮又急急地朝下一个新生奔去,看见你心底最原始的野性,看见不经雕琢的诗意,看见饱经风霜的平淡,看见一朵朵花蕾托起万千星云。
戏台
(初赛一等奖)
高2019级12班 辜阅
离进场还有两个钟头,观众们的喧闹声就大得里屋都听得见。万老板腆着肚子窃喜地来回踱步,瞄着一旁悠闲地喝着浓茶的杨筱林,他似乎觉得自己有些不文雅,忙自以为斯文地推了推他那副并没有镜片的金边眼镜,满脸讪笑地开口:“角儿,咱这主办方做得够讲究吧,多大的戏台,多好的设备!”说罢他又扶了扶镜框,见杨筱林不开口,不甘心地添上一句:“诶,就这剧场号称北京造价最高的,我可是跑了半个月才敲下来的,真真的够气派!”谁知杨筱林只从鼻子里轻笑一声:“倒还不如小园子。”万老板碰了一鼻子灰,笑僵在他肉沟纵横的脸上。筱童忙打圆场:“万老板,我师哥是怀念小园子气氛好。”万老板忙接下话头:“是是是,我们这些粗人不懂了。这样,角儿您先歇着,一会就开场了。”说罢忙不迭点头哈腰退了出去。
“师哥,生意人就这么没心肠,当年剧社困难的时候他可不这样,是不是?”
杨筱林没有回答,他的确是忘不了剧社关门前,万鸿年是怎么说的。那年他也是这样腆着肚子,脸上的肉戏谑地揉在一块:“我到哪里去给你找好剧场?这年头谁还听你咿咿呀呀唱戏啊,明眼亏本的买卖你另请高人做。”
那属实是一段苦不堪言的日子,演艺圈群星鹊起,流行歌传遍大街小巷,听戏的人越来越少。最难堪的一次,台下就一个观众,上边演员正唱到节骨眼,观众手机响了,台上台下大眼瞪小眼,都愣住不知怎么办,最后杨筱林实在没辙,只好说:“你先接电话,回来咱么接着演。”
京剧走到头了,大家都这么说,大大小小的戏班陆续解散,好些人转了业。筱林的师哥筱其认识了个唱片公司经纪人,三言两语就把他捧得飘飘然的,隔天就和师父大闹一场,毅然决然退出师门要去当流行歌星。老师父拖着着病弱的身体拗不过他,只能看着他头也不回地走出去,自己佝偻着抹眼泪。筱林劝他留下,说咱们师兄弟十几年,师父病这么重,无论如何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忍下得下心?筱其翻翻白眼说,筱林,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份上也不跟你含糊,我早看那老东西不顺眼了,亏得我还以为做这个能大红大紫。唱流行歌来钱多快呀,兄弟,别傻愣愣地还守着破戏班子,早点去唱歌得了。杨筱林气得瞪眼,只憋出一句我的事不劳你费心,我就在这守着师父。
戏班终究还是没能支撑下去,来年倒春寒里,师父没撑住也走了。临走时他摸着筱林和筱童的头说,你们是好孩子,将来要是做别的也能有出路,不过做什么都得记得,先问问自己的心,筱林筱童含泪答应了。凋敝的戏园很快被人买走,杨筱林坐在门口看着物件一件一件被搬走,想起小时候他在后院里练功,天亮就起来吊嗓,到了晚上戏一开场,他就猫在戏台柱子后面张望,台上锣鼓一响,张君瑞月下跳墙;清风亭前父子恩断,老人垂泪哀唱。再大一些师父允许他挑大梁,他头一场就扮了杨六郎,白袍小将,披风一扬好不威风,他飘飘然地就唱完了全场,只记得台下掌声雷动,他觉得脸上因激动泛的红连脂粉也掩不住。他每天都听着过去老先生的磁带入迷,廉颇负荆会相如,萧何月下追韩信,每个故事都牵动他的心弦,他听师父说,现在好些人不听戏不懂戏了,因为他们都没机会接触,咱们要做的就是踏踏实实唱,让人们看看先辈们留下来的东西。
戏班子没了,筱林和筱童去四处不同剧院里打杂演一些小角色,等凑够了费用,结识了几个和他一样不灰心的演员,他们又租下小剧院重登舞台,他把心思都扑在创作和表演上,刚开始演出不多的时候,他就研究剧本那些人物的冲突,有意思有层次的唱段都拎出来,反复咀嚼研磨。他时常想起梅兰芳大师大改剧本,跳出封建礼教,塑造了无数灵动丰满的角色,让京剧在民国热潮达到了顶峰。历史上向来是戏曲适应观众,观众不爱看了,必定是京剧的形式内容跟不上时代了。那么老先生做过的事,他也来学习,曾经冷门的剧目删改重创,次要角色为他们再编情节,甚至外国歌剧也大胆改编融合。令人惊喜的是,竟受到了观众的好评。不知何时起国风回潮,人们再次追捧起传统艺术。杨筱林剧社的剧目新颖而精美,一下吸引了人们,剧社迅速走红,场场都座无虚席。
乐队在外边转轴拨弦地调音,杨筱林从回忆里抽身出来,坐到镜子前抹油彩化妆,场务走进来说:“杨老师,外面有个人说是您的老熟人,坚持要见您。”人话没讲完,一连串笑声就抢着冲进来:
“哈哈哈,兄弟咱们真是有日子没见面了。”竟然多年未见的曹筱其。他离开剧社头一年的确唱了些跟潮流的商业歌曲捞了一笔钱,只不过很快淹没在流量的浪潮里了。
杨筱林手上上妆一点没闲着,冷冷地问:“你来做什么。”
“我?弟弟开了专场大演出,我这不得来给你助个威?”
“这倒麻烦不到你,听外面就够热闹了。”
“哈,可不是嘛,咱这传统的东西才是耐听呢。现在的观众都好这口,听流行歌都得加那么几句戏腔才过瘾呢,哈哈。”筱其顿一顿,砸砸嘴又说:“你现在是大红人了,咱们这剧社招牌一打出去,可不是响当当的?”
杨筱林把小刷子往梳妆台上一砸:“怎么,想来挂个牌?”
“哎哟……话也不能这么说,那些年我也给剧社做了不少贡献,老头子那时总让我演重头……”
“你也有脸提师父!”杨筱林冷笑,“师父从小怎么教的我们尊师重道,你倒是一个字也没占。曹筱其我告诉你,路是你自己选的,由不得后悔!后台不留闲人,你请回吧。”
曹筱其还想说些什么,回头看见筱童叫来的两个保安早就气势汹汹地站在门口,只好憋着这口气退出来。
杨筱林长叹一口气,深深凝视镜中已扮上的脸。他好像看见了儿时登台脸蛋画得红扑扑的自己;第一次挑大梁时意气风发的自己;冷情岁月里曾迷茫落魄的自己;以及剧社重振阶段全力奋斗的自己。无论生命哪个阶段,哪种境况下,他始终是他,那个天真坚持着毕生所热爱的人。
大幕开,京鼓起,又该登台了。



全部 0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