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素芬朗读沈心同学获奖佳作《江南清歌奈何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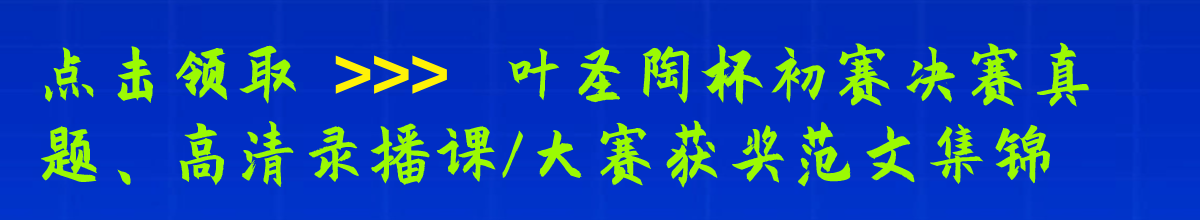

读者简介: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第二中学的陈素芬。在日常生活我喜欢朗诵,阅读,此次被这篇《江南清歌奈何闻》所吸引,希望我的声音能够带大家走入江南水乡。
江南清歌奈何闻
沈心(浙江省湖州中学高一)
在江南的莲叶田田里,时光随清泉流淌,与每一块卵石的相遇,都由浅浅的波纹诉说。其间糅杂进了姑娘们的菱歌,小儿的笑闹和老者的低语。多么奇妙,江南的清歌,从千百年前的源头,就这样一点一滴流进了每个江南人的心。
东晋有个桓子野,一听到清歌,就会不由地唤“奈何”。这是谢安口中的“一往有深情”,其实是每个人对生命魅力最心底的赞叹,为自然文化最虔诚的折服。
想到我小时候,大概只会摇摇摆摆学步的时候,外婆常常抱我去外婆家旁边的莲花庄,据说是某个文人雅士的宅院,其实也无从考证,只记得那里有一个大池子,白玉拱桥下大片的荷叶,在小小的我看来已是奇景,至于那句“接天莲叶无穷碧”就和这个画面绑定在了一起。那些荷叶上啊,总是飘着歌声,轻轻地,弯弯绕绕,悠悠转转,我相信那应该就是吴歌了。那是我们这儿的老人们,轻轻唱和,听不清唱词,却听得清她们年轻时的江南情调。稍大一点的时候,听外婆说,我竟然会咿咿呀呀地跟着,甚至手舞足蹈,来一段即兴伴舞。“你那时候可不怕尴尬,是大家的开心果。”外婆总是笑着说,让我不好意思起来。
初中的时候,我也不知为何加入了一个“湖剧社”,也不知为何学校里会有这样一个社团,那是很小众的戏剧,我们湖州土生土长的,甚至也许很多本地人都不知道的。唱词用的都是吴语,也就是我们的湖州“土话”。我当时好像有些什么触动,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说过湖州话了。其实,读幼儿园之前我一直说的湖州话,而且非常地道,甚至会说一些湖州话独有的词语和句子。比如现在人们用湖州话说“下雨”是“落雨”,但外公教我的是“豁落”——一个不知道怎么写出来的词,两个入声字,利落爽快。外公很喜欢逗我:“豁落否豁落啊?”我就会颠去阳台上往外张望,高兴地喊:“否豁落!”但上了幼儿园,全班只有我一个小朋友说的是方言,别人说“虾”我就说“弯攒”,总是被大家笑。因此我“痛改前非”,一两个月就学会了普通话,还经历过一个用普通话的语调“翻译”湖州话词语的让人哭笑不得的阶段。但我从此不太愿意再说湖州话了,饶是外公严厉地让我用湖州话跟他说话,我还是慢慢地变成了只会听不会说,有时要说两句舌头也像打了结不利索。
然而湖剧让我发现,“土话”竟然也能唱进歌里,那么独特的歌,不是京剧的庄重富雅,而是淡淡的,一唱三叹,正像记忆中莲花庄里的低吟浅唱。其实我根本没学会些什么,但我却发现了藏在身边的江南韵味。在每天出门时外婆的一句“百坦”里,就是我们的慢文化:不要急躁、凡事坦然的叮嘱,我们当做“再见”来用。很多外地人对湖州城、湖州人的最大印象就是“温吞”。“百”是入声,而“坦”有三个转音,说起来必得拖得长长的,总让我想起湖剧的宛转来。原来,我每天听到的话便是江南最独特的清歌:没有伴奏,有的是九声八调,古朴而清丽。湖州话非常接近古语——有些看上去不押韵的诗用湖州话读就押韵了。从“鱼戏莲叶间”,到“桃花流水鳜鱼肥”,再到“寻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我发现原来我就生在诗词里的江南。
我所遗憾的,是曾经熟习的方言已很难让我亲口说出。这大概也是许多方言现今的困境。其实方言一点也不“土”,它承载着一种地域文化最深层的精神,最坚固的根基,是需要我们共同守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多么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开口,用乡音诉乡情。
虽然自己说不好,听闻家乡话,总是有种亲切的感动。那几句湖州话,是梧桐树下竹躺椅上大蒲扇摇来的,是满布青苔的白墙黑瓦弄堂风吹来的,是笼着晨曦的早点摊上混着茶糕和青团香飘来的,带着湖州人慢悠悠的生活哲学,藏着心底对家乡风土的一往情深。在压力渐增的现代社会中,也许生活节奏不能像从前那样慢,但听着湖州话,一种温吞坦然总是存于心底,为我抚平生活中的焦躁不安。
“一往有深情”,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对这江南的情早已融于血液,在我心中不停歇地流淌。清泉叮咚,清歌缥缈,我心中的那句“奈何”也许已不用说出口。
(指导老师:王湘萍)



全部 0条评论